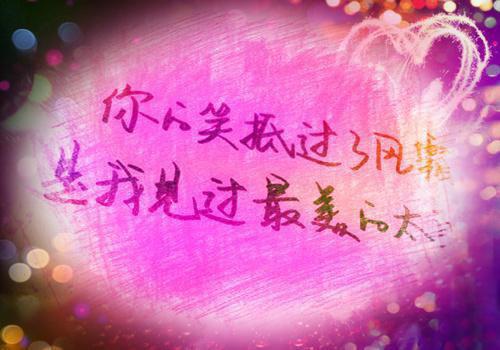平原上的摩西讲的什么 平原上的摩西故事梗概
《平原上的摩西》故事发生在1983到2007年这24年之间的沈阳:主人公庄树和李斐是儿时的邻居和玩伴。庄树的父亲庄德增是“从市卷烟厂脱离了关系”单干的烟草商,母亲是有绘画才能的基督徒;李斐的父亲李守廉是拖拉机厂老实稳重的钳工,母亲早已过世。1995年,庄家搬走,两家再无音信。庄树长大后当了刑警,参与调查1995年的警察被伤致死凶案,却逐渐发现李斐父女卷入其中。最后见到李斐时,庄树发现自己亦是凶案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故事发生在1983到2007年这24年之间的沈阳:主人公庄树和李斐是儿时的邻居和玩伴。庄树的父亲庄德增是“从市卷烟厂脱离了关系”单干的烟草商,母亲是有绘画才能的基督徒;李斐的父亲李守廉是拖拉机厂老实稳重的钳工,母亲早已过世。1995年,庄家搬走,两家再无音信。庄树长大后当了刑警,参与调查1995年的警察被伤致死凶案,却逐渐发现李斐父女卷入其中。最后见到李斐时,庄树发现自己亦是凶案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这样说起来,《平原上的摩西》似乎只是一篇满是巧合与安排的悬疑故事。但双雪涛并不满足于此:他将一个从“青梅竹马”到“各自天涯”的故事嵌在了当代中国改革史之中,使人物的命运与脚下的土地发生了深刻的联结。
一、生于1983
1983年是庄树(以及双雪涛本人)出生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大陆发生了两件与这篇小说相关的大事。第一件是“严打”。“文革”中,固有的社会筋脉被打断,释放出大量的人力物力,一时间无法得到顺利的疏解,恶性犯罪集中爆发,拧紧了人们的神经。为此,中共掀起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运动。
这次“严打”共持续三年,之后在1995年、2001年和2010年又开展了三次。小说中的沈阳“二王”案,就发生在第一次“严打”之前;另外,后来的出租车司机连环被杀案(以及现实中广受关注的聂树斌案),发生在第二次“严打”之前。在小说中,这些被“严打”的对象,似乎更多地是为时代所迫的“多余人”。例如,小说中的“二王”案就充满了良人走投无路的悲剧感(现实中或许不尽如此)。
1983年的第二件大事是“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件事与《平原上的摩西》并无直接关系,但它潜藏在1980到1990年代之变的脉络中,为双雪涛的写作划定了空间。你可能没有听说过“清污”运动,但应该听说过《怎样鉴别黄色歌曲》这本奇书。它出版于1982年,其中批判了《何日君再来》等毒害中国人民心灵的黄色歌曲,可以被视为是“清污”运动的前兆。
这场“清污”很快便由于胡耀邦等人阻拦而草草收场,但它的影响却比“严打”深远得多。从政治上看,其中暴露出来的高层矛盾直接关系到胡在1987年的下台。从文学上看,“清污”运动是促使当代文学发生“寻根”和“先锋”之变的一个历史契机——后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很多作家,都是在这二者开拓的空间中继续前行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脉络存在,我们很难想象双雪涛(以及更多的作家)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写作,或者会不会成为作家。
因此,无论从小说的故事、形式或者双雪涛的写作本身来看,1983年都是一个原点。此时,中国的改革刚开始不久,那些心思活动的人(如庄德增,曾经是敢想敢打敢干红卫兵头目)趁着风势及早起飞;而另一些,更多的人(比如李斐父女),则在为发展付出足够多的代价之后,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包袱和阻力。就这样,小说中的人物来到了1990年代。
二、定格1995
相比于1980年代,中国的1990年代呈现出更加复杂的面相:前者为后者开辟了空间和路线,后者继承了空间,但借着1980年代末的动荡摆脱了路线,肆意飞奔,左突右撞。再加上时间距离尚短,关于这个年代的解读尚显得不足。不过,近些年来这种解读处于快速增长的状态,接下来定会成为一股热潮。
有趣的是,与“二二八”之于郭松棻、“启蒙时代”之于王安忆的情形类似,1990年代是双雪涛的少年时代。因此,他笔下的1990年代,是记忆驳杂模糊但感觉鲜活的时代,是经历过但当时不可能理解的时代,是需要不断重访以及重读的时代。
小说将叙事的重心放在了 1995年。这一年,曾赶上1980年代初“下海潮”的庄德增已经是成功的烟草商人,而李斐的父亲则遭遇了“下岗潮”。“潮”这个字眼实在是近四十年的“时代汉字”: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和什么时候结束,但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被其推搡前进或拍打在岸。
两年前(1993年),中共提出建设市场经济,各种深层的经济改革开始,同时伴随着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和大量的下岗(也就是1995年“严打”的背景)。这些矛盾,在双雪涛出生成长的东北地区尤其突出。例如,在调查1995年出租车司机连环被杀案时,警察蒋不凡说:“最近满大街都是下岗工人,记得我们前一阵子抓的那个人?晚上专门躲在楼道里,用锛子敲人后脑勺,有时就抢五块钱。”
正是“下岗潮”和“严打”这两个相互关联的事件,将李斐的命运定格在了1995年。庄树家经济发达,使他们有可能搬离原来的住所,而李守廉只能靠贩卖小商品来艰难度日。为了纪念和告别,李斐向庄树许诺,要去沈阳铁西区艳粉街附近的高粱地放一把“烟火”,于是谎称肚子疼,与父亲乘坐出租车去那里的中医诊所看病,却被伪装成司机的蒋不凡误认为是连环杀手。途中,蒋不凡在黑暗中停车盘查,不幸遭遇车祸;李斐伤及脊柱致残,李守廉趁机重伤蒋不凡。结果,父女两人此后过起了隐匿与伪装的生活。
然而,双雪涛利用多视角叙述的形式,一边将上述核心场景包裹成谜团,一边将谜底的揭晓延滞到小说的最后。这种曾被福克纳、芥川龙之介和乔治·马丁等作家用到极致的形式当然并不新鲜(甚至,双雪涛的多视角叙述并未成功地表现出人物个性和声音的多样性),但它通过重组时间脉络,很好地展现了1990年代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也再现了双雪涛对其经验进行重读的过程。
正如隐匿的李斐父女一样,双雪涛所读取的1990年代是一段正史不载、野史不闻的伤亡史。它被隐匿在发展的承诺中,被隐匿在GDP的双位数增长中。当这种历史被揭开时,一道从1980年代开裂的鸿沟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于是,在小说的最后,2007年,当刑警庄树和嫌犯李斐各乘一条小船在公园湖上见面时,能够“走过”他们之间水面的,只有画着他们童年游戏场景的烟盒。这一童话般的结尾虽然足以赚得眼泪,但它透露着现实中跨越鸿沟的不可能,以及作者笔力尚欠时的不得已。为此,我对双雪涛未来的作品保有最高的期待。
三、小说·时代·国家
哈金说,“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主题应该是个人与国家、种族的冲突,这个说穿了是政治性的问题。”在双雪涛的小说(以及很多当代中国大陆小说)那里,我们似乎看不到国家的存在。但是这里却有国家的另外一个假面——时代。平原上的故事从“文革”延伸到当下,但其重心却位于1990年代,往前往后都只不过是这个重心的前因后果。这个时代借助国家的力量,不由分说地裹挟着一切。它肆无忌惮,以至于无论你躲到哪里,都必须意识到你永远是它的一部分。只可惜,不同的部分之间的差别是那样的大,大到你只能隐忍地对昔日的同伴说:“你长大了,很好。”更令人诧异的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成为这个这个时代的一部分的方式是被抛弃或被遗忘。如哈金所言,“我们创造了国家,国家却失掉了我们。”在这里,每个人都参与了创造时代的过程,但很显然,小说中的大部分人都失去了这个时代。或者说,这个时代失去了他们,像跑得快的人丢下残疾者一样,把他们留在了黑夜的郊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