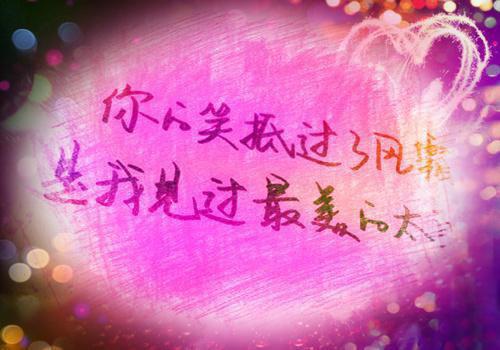二亩台台旧事全文阅读(黑娃,台台,柿子)最新章节_二亩台台旧事全文阅读
辣子馍 烧红薯
1
村里大人都下地干活去了,二亩台台一拃长的土街上,寂静得只有鸟儿飞过的影子。我们小孩没有事,站在家门前的麦场里看风景。说是看风景,也就是一种说法,待在麦场总比呆在家里要眼界宽嘛。
时令已到了白露,早晨起来,向山上山下望去,烟气迷蒙,山色不再像从前那样绿意盎然,大地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繁华热闹。一台一台耕过的田地,呈现出黄土地原有的本色,在清冷的秋光里,寂寞地等待着又一轮播种麦子日子。不过,在层层的梯田中,却夹杂有少许的秋庄稼地,地里生长的玉米、高粱、糜子和谷子,它们金黄或嫣红的景色,与这草色衰微的秋景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我们几个小孩站在麦场边,望着深秋的田野,却有些熟视无睹。倒是长在麦场边的野酸枣树,枝丫上密密麻麻正在上色的酸枣,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站在崖畔边随意地摘着吃起来。吃了一时,大怪说:“咱不吃酸枣,咱吃烧玉米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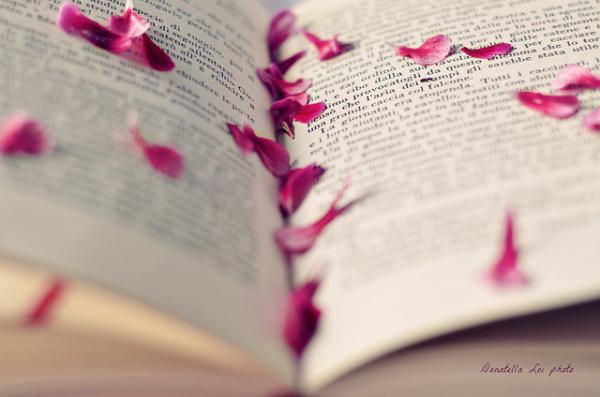
黑娃说:“玉米地有大人看护,红薯地里没人看,咱吃烧红薯走。”
我高兴地说:“我回家给咱取铁铲铲和火柴,咱去‘兔嘴’,那里红薯最甜,像毛栗一样好吃。”
“兔嘴”是村里大人给山上边一块地起的名字。因为站在远处看,呱啦鸡岭延伸下来的这个山嘴形状像“兔嘴”,也因为在冬天的日子,兔子经常在“兔嘴”下边这块地里晒太阳。我们下雪后去上山玩耍,经常看见兔子在雪地上玩耍时留下的蹄印。
2
我跑回家拿了铁铲铲和火柴出来,却看见戴着“瓜皮帽”穿着夹袄的四爷正牵着“叫驴”(1)向麦场边的石碾子走去。二狗笑嘻嘻对我说:“四爷碾辣子呀,咱吃油辣子馍。”
我们围了过去,看着四爷把“叫驴”套上碾子,又给戴上“暗眼”(2),把提笼里的干辣子顺着碾盘窄窄倒了一圈。“叫驴”仿佛能看见似的,没等四爷吆喝,就拉着碾子走动起来。四爷拿着笤帚一边扫辣子一边问:“想吃油辣子馍?”
我们齐声喊:“就是。”
四爷一笑说:“我把辣子碾完,就给你们碾油辣子馍。”
我们眉开眼笑,都转身向家里跑去。
我取了一个蒸馍,用刀切成三片,向馍上撒了一点盐,拿着又跑回麦场里。转眼,大家都来了,笑笑地站成一排,看着驴拉着碾子转圈圈。看着看着,我眼前就有点恍惚,感觉整个二亩土台台都跟着碾子转动了起来。
四爷用铲子划拨着碾盘上的辣子说:“再转几个圈圈就好了。”
大怪问:“四爷,再转几个圈圈就好了?”
四爷说:“再转十个圈圈。”
大牛就带了头,我们一起大声数起来:“一个圈圈、二两个圈圈、三个圈圈…… ”等数到第十个圈圈,四爷说碾好了。
四爷用笤帚把碾好的辣面扫到一块,用铲子铲到一个大老碗里,一转身笑道:“来,给你们碾油辣子馍。”
我们笑嘻嘻把切成薄片的馍,放在粘满红辣子的碾盘上。四爷也从自己提笼里取出几片馍放在上边。“叫驴”再次拉着碾子转动起来。几圈转过,切成薄片的馍,碾成了又大又红形状各不相同的薄饼子。
四爷给“叫驴”卸了套,拴在麦场边的槐树上,把自己的油辣子馍铲着放到老碗里,还用笤帚把留在碾盘上的馍屑扫到一起,低下头用***着吃了。
四爷牵着驴走了,我们眉开眼笑爬到碾盘跟前。我嫌戴在脖子的“红缰绳”(3)碍事,把它甩在脖子后边。留在碾子上的辣子,应该是辣子的精华,我吃了一口,就把眼泪吃了出来。我抬起头吐着舌头看大家,每个人和我一样,吐着长长的舌头吸冷气。等这阵辣劲过去,大家又低下头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笑一边吸冷气,吃的是龇牙咧嘴,吃的是有滋有味。很快,油辣子馍就吃完了,我们也学着四爷的样子,用舌头把碾盘子上的馍屑***吃光了。
太阳已经升到树梢头,窄窄的土街又安静下来,有的院落窑背上升起做早饭的炊烟。
3
我们吃了油辣子馍,把烧红薯的事暂时忘在了脑后,跑到涝池岸边懒洋洋躺到草坡上,漫不经心望着山上山下的田野。隔沟对岸,石马岭的人正沿着蜿蜒的山路向山岭上边的村子走去。沟坡这边,二亩台台在地里干活的大人,也沿着半沟里窄窄的山路向村子上边走来。
突然,从生产队麦草园里传来一阵急猛的狗咬声。大牛说:“是我家‘二黄’又和‘四眼’咬仗呢。”
二狗的深窝窝眼一闪说:“你家‘二黄’咬不过我家‘四眼’。”
大牛说:“咋不说我家‘二黄’受伤了。”
二狗说:“你家‘二黄’不行,才叫貒咬了。”
大牛生气地拽了一下二狗的“气死毛”(4)说:“你家‘四眼’才不行,一看见貒就吓得趴在地上都不敢动了。”
二狗着急地说:“你看见了?”
大牛笑道:“我大(父亲)说的。”
二狗说:“你大才胡说呢。”
大牛说:“我大咋不说‘大黑’往地上趴呢?”
“大黑”是我家的狗。听着大牛的话,我有点洋洋得意,接住大牛的话说:“貒争得很,很多狗都咬不过。那天晚上,我家‘大黑’把貒撵到一个水冲窟窿,大人用铁杈才把貒戳死了。”
大怪说:“这两天玉米地里又有貒在糟蹋玉米,我大说今晚上大人又到地里去撵貒。”
大牛笑道:“人还没吃玉米,戳先吃了。”
我说:“貒的鼻子灵得很,隔着皮都能看见里边玉米好坏,专检好玉米吃呢。”
石马岭村的人走得看不见了,二亩台台的大人走到涝池岸上。有人看着我们笑道:“就当娃幸福,啥心都不用操。”
有人说:“回家吃饭走。”
我们齐声喊:“不饿。”
有人笑道:“你们为啥不饿?”
我们嘻嘻地笑着说:“我们吃了油辣子馍。”
大人回家去了,大牛想起了烧红薯。我说:“我取馍把铁铲铲忘到家里了。”
二狗说:“我回家给咱取铁铲铲。”
二狗回家去了,不但取来了铁铲铲,身后还拉了几根椿树枝条。前些天,六伯把家门口一棵春树挖了,想打架子车车厢呢。
4
大家高高兴兴向窑背上边的土台台走去,来到生产队的麦草园外边。二狗拉着椿树枝条在墙外边等着,其余的人从墙角的豁口爬进去,每人在麦草垛上撕下一小抱麦草,又从豁口爬了出来。
我们心怀喜悦,有说有笑向呱啦鸡岭南坡下“兔嘴”那块地里走去。“兔嘴”这块地是“料僵石”(5)地,长庄稼不行,长出的红薯却特别甜。我们来到“兔嘴”地边,去年我们在土崖上挖的烧红薯的小窑窝还在。它就是在土崖上挖一个土窑洞,在土窑洞周围放上一圈石头,把红薯放在石头上,在石头底下烧火。至今,还能看见去年在土窑窝里烧红薯时,烟熏火燎留下的痕迹。
我们把椿树枝和麦草放在地上,一起走进红薯地里。我们已经有经验,并不是随便乱挖,先是拨开红薯蔓,看根部周围的土是否拱起来,地面上是否有裂缝。如果没有,就说明土里的红薯结的少,个儿可能还小。如果拱起的地面上有裂缝,我们才用铁铲铲去挖,等把红薯一个一个挖出来,再用土把挖的坑填平,把红薯蔓扯得平平展展,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一般情况,“料僵石”地里长的红薯多半小而细长,特别的红。我们掏了五六窝红薯,抱着来到土崖下。大怪放下手里的红薯,回过头看着红薯地笑道:“一点看不出来我们把红薯刨了。”
黑娃笑道:“就是,一点都看不出来。”
我也说:“就是看不出来,和原来一模一样。”
大牛却说:“我看别的红薯蔓叶子都端端站着,咱刨过的红薯蔓叶子都东倒西歪。”
二狗笑道:“大人看出来也不怕。”
黑娃笑笑地转过身,把红薯一个个放到土窑窝两边的石头上。
大牛往土窑窝里放了一把麦草,要过我手里的火柴擦着了。麦草呼呼地燃烧起来,青烟顺着土崖往上升,还没升到土崖上头,就被山风吹散了。
大牛往里边添着麦草,黑娃拿起一根树枝在拨火。大怪在后边拽了一下黑娃的“小辫子”(6)说:“不要拨火了,要慢慢烧呢。”说着把黑娃挤到了一边。
我和二狗把椿树枝用脚踏着折成许多短节,递给大怪。椿树枝在麦草火里很快燃烧起来。
等了一时,等火小的时候,大牛爬到土窑窝跟前,用树棍把红薯翻动了一下,把之前烧的灰烬往两边拨了拨,和大怪一起给里边继续添火。
太阳已经升到天空最高处,田野里一片寂静,偶然有野兔从地坎上跑了过去。
又添过几次火,大怪碎鼻子一耸说:“能闻见烧焦味了。”
我们停止了添火,坐在一边耐心地等了好久,才用树棍把红薯一个个拨出来。红薯被烧得黑乎乎的,焦味比香味还重。
又等了一时,我们用夹袄下襟撩着黑乎乎的红薯,向土崖上边的草坡跑去。
坐在山梁上,眼界很宽,心情也好。我们一边看着山下纵横交错的山地一边吃起了烧红薯。
黑娃说:“好吃的很,比家里的红薯好吃。”
大怪说:“在家里吃红薯有啥意思。”
我突然着急地喊:“快看,野鸡。”
一只毛色斑斓的长尾巴野鸡,从山根下的小路上跑了过去。
大牛问:“野鸡吃啥?”
大怪说:“吃虫虫草草和蚂蚱。”
大牛问:“吃红薯不?”
二狗笑道:“野鸡咋能吃红薯,这是人吃的。”
我想起夏天山坡上飞的呱啦鸡,问:“呱啦鸡吃啥?”
二狗说:“都是鸡,吃的一样。”
我问:“呱啦鸡现在飞到哪里去了?”
黑娃说:“谁知道,反正明年夏天就飞回来了。”
大牛看着二狗笑道:“你把嘴吃成黑圈圈了。”
二狗看着大牛说:“你也一样。”
大家一个看一个,哈哈地笑声一片。等吃完红薯,一起舒舒服服躺在草色泛黄的山坡上,望着头顶上碧蓝的天空。一群乌鸦在山顶上无声地盘旋。山崖下边,传来野兔吱吱的咬仗声。空气中,飘散着玉米、高粱、糜子、谷子和大豆甜丝丝的味道。生长在山坡南边的柿子和野酸枣,明显比别的地方要红亮,大地又一年在演绎着春花秋实的故事。
太阳向西边越走越远,二狗竟然拉起了鼾声。我躺在山坡上,望着头顶的云朵发呆,就是不想回家。太阳在落山,山上的冷气上来了,我们一起向山下走去。回到村子,有大人已经拿着铁杈圪蹴在麦场边的碌***上说闲话。我家的“大黑”和村里几只狗,大概知道今晚上要去玉米地里撵貒,就特别兴奋,相互在麦场里追逐耍闹。大人看见我们,没有谁问为啥这么晚才回家。我觉得在深秋的晚上,月亮底下拿着铁杈带着狗在玉米地里撵貒,特别的有意思。
注:
(1)“叫驴”:公驴
(2)“暗眼”:遮挡牲口眼睛的护罩。
(3)“红缰绳”:用上蓝下红的布料缝制的,形如“8”字,戴在小孩脖子上,用来祈福。
(4)“气死毛” :父母在小孩脑袋后边留的一撮头发,俗语叫“气死毛”。据说,小孩哭得岔了气,大人把“气死毛”揪几下,就哭出声来了。
(5)“料僵石”:快要石化的硬土疙瘩。
(6)“小辫子”:父母把男孩当女孩养,在脑袋后边留的一根“小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