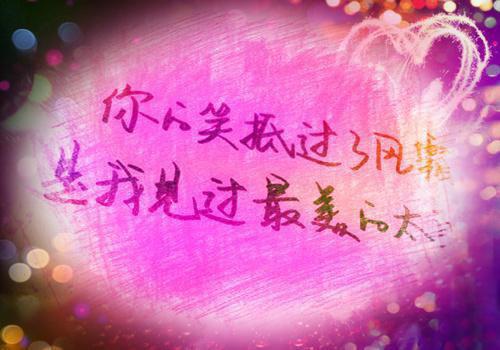谭嗣同和他的时代全文免费阅读_谭嗣同和他的时代最新章节
1
在漫长的19、20世纪之交,湖南一带所汇聚的真实和想象的能量,汹涌激荡,为旧时中国所罕见。而浏阳则是大河滔滔中的一条支流。据《湖南通志》记载,浏阳河又名浏渭河,原名浏水。浏,清亮貌。因县邑位其北,“山之南,水之北,谓之阳”,故称浏阳。浏阳地处湖南东部,毗邻江西。三国时属吴地,开始设县,隋时并入长沙县,唐时复置浏阳县,元时升为州,明洪武时复为县。
中国人对于浏阳的印象大多起于那首名为《浏阳河》的民歌。民事如歌,大河款款,时间是一条越流越宽的江河,摆渡往事,也模糊记忆。浏阳河有两处源头,一为大溪,一为小溪,分别出自罗霄山脉北段大围山的北麓和南麓。两处溪水经过大半个浏阳,于城东汇合。一入长沙,浏阳河便如同豪情万丈的少年,突然高门亮嗓,陡然生变,将它的叛逆不羁,一股脑甩给了身后的浏阳。人善变,河流因势也善变,变与不变都由不得自己。无论智者乐水,还是仁者乐山,浏阳兼具这人生中的两重境界。许多年前,我在一个秋日的黄昏抵达长沙,绵长的枯雨期拖瘦了湘东一地的河流。展现于眼前的浏阳河,失去了印象中九曲十八弯的缠绵。像是经历过大场面金盆洗手的江湖客,老成而不无世故地经营着自己的余生,令人神迷遐想。
人迹于水,水势浩渺;人迹于清冷的古物建筑,往往会给枯萎的时间带来“回阳”的血色。人的足迹所到,得所应得,失所应失。行走于三湘大地,做个时间的旅人是个不错的选择,稍不留神便与名人的故处摩接。浏阳河流域自不例外。他们或以文,或以歌,或以教,或以义,或以战,甚至或以死丰富了浏阳的外延。可以说,千古之下,能够彪炳湖湘称为人中之龙、学术北斗的,不在少数。尤其近一百多年来,众多湖南人跻身中国近代史舞台的聚光灯下,各展其能,各表其事,各安其命,又各行其道。而在这其中,谭嗣同无疑是划过浏阳天空最耀眼的那颗彗星,一闪而逝。

翻阅史料,突然理解了海德格尔的那句话:“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之上绝无尺规。”这世间人事,也暗合了“道法自然”的隐喻。奔走于大地上的真实,是自由的,安稳的,不应被打扰的。就连我这漏洞百出的书写,也是一种打扰,自以为是的喧嚷,不可饶恕。当车驻于浏阳北门正南路上,我试图寻觅那条通往谭嗣同故居的梅花巷,遗憾的是,在分布着医院、学校、剧院等数十家单位的街面上,那条在老浏阳人记忆里青石铺路的巷子了无踪迹。据明、清时期《浏阳县志》记载,此街面有一条南起粮仓街,北至圭斋路,全长两百多米的街巷。巷道为青石板铺垫,巷内有宋家大屋、谭家大屋、黎家大屋、贺家大屋等。其中黎家大屋有个叫“梅花碧境”的地方,种有多个品种的数株梅花,芳香溢满整条街巷,所以人们也称为“梅花巷”。
谭嗣同的先祖于清朝道光年间迁居浏阳,居住在梅花巷丹桂坊。四时有序,日月更迭,待到谭嗣同的祖父时,又迁回到梅花巷居住。随着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一路升迁至湖北巡抚兼湖广总督,谭氏家族进一步发展壮大,在靠近梅花巷不远的浏阳北门建造了一所“大夫第”,即我们现在看到的谭嗣同故居。梅花巷顺延而下便是浏阳河,此处是一座有着风霜压身的老码头,样貌古旧,凋零落魄,入不得世人挑剔的眼。谭嗣同称湘人不幸处于未通商之地,“不识何为中外,方自以为巍巍然尊”。没见过世面,还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嘴脸像极了那个老朽的帝国。《湘江评论》以同样的口吻写道:“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
待到清朝中后期,这里渐渐有了商业气息。水、桥、船将此地与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不安分的人们开始奔向更广阔的空间,染世渐深。从浏阳河经湘江至长江,可以到汉口等大城市。浏阳大围山的木材通过放竹排,可以从上游运到浏阳,再经过浏阳转运至长沙等地。而浏阳的花炮、夏布也是通过水运运至汉口,再销往世界各地。晚近以来,从汉口来的轮船带来了洋油、洋火、洋碱、洋布等洋货。航运码头水运的发达,也就此改变了城市的面目,让它变得愈加繁荣。一时间南北通衢,商贾云集,很多商人在浏阳置地置业,娶妻生子。梅花巷里的很多四合院便是那些赚了大钱的商贾巨富建造和买下的。谭嗣同的故居也在其中,临水而立,既融于其间,又有几分遗世独立的意味。
走出文庙数百米,几分钟就可以走到谭嗣同故居。故居为砖木结构,三进院布局,前栋临街,面阔五间,中堂与后堂之间有一过亭,过亭上方有长棱形六角藻井。屋子两边设置风火山墙。据说这栋房子建于明朝末年,最初是一个祠堂,被谭嗣同祖父谭学琴买下作为私第,并改造成现在的三栋二院一亭,一座天井式民宅建筑。宅子的精美也不是普通民宅可比,尤其房屋的木雕,十分精美。屋子的梁架、斗拱、雀替等,均有雕饰图案,正厅屏门以及几处花窗更是木雕杰作。
用手触摸老房子的门墙,如同触碰一段老旧时光。脑海走马灯似的浮现一幕幕历史故事。偶有三两个调皮的小孩,在身边穿插嬉戏,倏来忽往,像是蝴蝶穿花,花不沾身。那一刻,让人觉得时间也跟着穿越了。谭嗣同出生时,这个家族已在湖南居住超过了十五代。十五代,我在心里默算着是多少个年头。不算则已,一算惊人。一个个念头在脑海里翻腾,不觉有了温度。再低头俯瞰橱窗里谭嗣同手书诗卷,墨迹苍茫,纸色苍茫,时间苍茫,弥漫着摄人心魄的旧气。翻开浏阳谭氏族谱,看到谭家从宋代一路发散出来的巨大脉络,如同一张蛛网。中国人使用“家族”这种巨大的传统来对抗动荡和王朝更替,个体依附于其间,寻求庇护,寻求血脉的递延。
据谭氏族谱记载,北宋末年靖康之乱,金人攻占北宋都城汴梁,中原汉人纷纷南下。谭氏的第一世祖谭孝成便是在那个纷乱的世道里,率领族人,颠沛流离,由江西之地迁往福建路汀州长汀县。南宋至元,谭氏也只是普通的农耕之家,在闽西一带山村开垦耕作。他们的命运如同那些名姓不彰、默默无闻的山间花草,在不起眼的角落繁衍生息,如同大地上的万般灵物。南宋末年,第八世祖谭启宇之兄谭启寰,任主管殿前司,后因抵御蒙古军南下,不幸兵败身亡。待到明朝开国,谭氏宗族开始崛起而以武功闻名于世。在头颅如灯笼一样明灭无常的时代里,武是取人首级的法门,武也是护住项上人头的法力。其实,它们是什么倒无所谓。那照亮一个家族命运前路的,就是灯笼一般的头颅。千灯万灯,点灯的人,要将属于他的那盏灯火传给后人。
洪武年间,第十一世祖谭如嵩追随燕王朱棣“宦游北平”,官任燕山右护卫副千户。其子谭渊继承父职,靖难之役随朱棣在北平起兵,每战必从,因功升都指挥同知,后于河北夹河之役阵亡。朱棣夺位成功,赠都指挥使,追封崇安候,建祠以祀,入《明史》列传。先人留下的遗泽,就像是人的脚印、车轮的辙迹,随着时间的流逝,渐行渐远,也渐渐淡去。后人留恋先人的流风余韵,莫若书写自己的历史。谭氏以武功著望于明,两百余年间,位列侯伯者九世十人。这段历史在谭氏后人心目中,已算得上足够显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反复记录,念念不忘,成为他们心中向往追慕的黄金时代。
谭氏于晚明之际迁居湖南,第十六世祖谭宗纶镇守湖广,久驻湖南,其子谭功安遂留居长沙府长沙县,立宅于四方塘,他是谭氏迁居湖南的始祖。待到明天启七年(1627),第二十祖谭逢琪带着弟妹子侄,又先后由长沙迁往浏阳定居。刚来到浏阳,谭家人虽然家境较为丰裕,但作为外人要想立足乡土之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容易。谭氏宗族迁居浏阳之时,正值明清易代之际。随着家族黄金时期的结束,谭氏又从勋贵阶层跌落至寒微家族。每逢清明或中元,谭家人在家庙举行祭礼时,总会对儿孙做出训诫。而那时,他们念念不忘的仍是“列祖勤王之功”,虽然那些荣耀已成为遥远的过往,留存于泛黄的谭氏族谱。这个世上没有一种传递能够特立独行地发展,如入无人之境。我们必须以人类精神的名义,感谢我们的先人,感谢他们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为另一头的我们做出的选择。一个家族伴随着王朝更迭,也在努力地适应时代,转变方向。
在此以前,谭氏以武功起家,重武轻文,用谭氏后人的话说,“先世将门,闳于武烈,文学无闻焉”。谭氏宗族的光荣历史,是先人们用人性的刚烈和刀马之功换来的。至于文学,于这个勇字当先的宗族而言,一度并无亲近之感。但到了谭嗣同的高祖谭文明时,举家迁至浏阳南乡吾田市,栖身山林,历经三世经营,家风随之豁然贯通。当然这也和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有关,承平日久,国家不再需要那么多武人,而转向以文治国,科举取士。一个有着两百年尚武之风的家族,由尚武转向崇文。谭文明的兄弟文魁、文开、文章,“一列府庠,一为修职郎,一为县试前茂”,都成了地方上享有君子之誉的人物。笃学固穷,文行有斐,谭家自此以诗书继世。他们期盼着家族中再次出现穿官服、挂朝珠的人物,那样的话,才能重新恢复先祖的荣光。
谭氏宗族弃武从文,耕读起家,靠着几代人的奋斗和积累,在浏阳建立了可观的产业。其时有乡人以羡慕的口气恭维:谭氏“从此步蟾宫,题雁塔,跨金马,登玉堂,直指顾间事耳”。在一个难以判定方向的世界里行走,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又如何知道自己是走向没落,还是走向昌明呢?如果说生存是智慧的本性,那么还有一种累世而成的神秘力量在冥冥中指引:一连串的偶然,才是必然。事后来看,如同暗夜灯盏,如同神谕,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谭嗣同的祖父谭学琴,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原居浏阳南乡吾田市,其父过世后,率诸弟迁居城内,居西城。谭学琴因父亲卧病在床,家道中落,便早早地踏足社会,成了一名谋食者。为了养家糊口,谭学琴跟着长兄谭学夔在县衙做了一名管理簿记的小吏,靠着打拼和积累,数年后,他们将家迁到浏阳县城的梅花巷丹桂坊。谭学琴为人豪爽,常助人于危难。据说,家中的抽屉里塞满了族人和亲戚打的借条。先人把他的光辉和德行,雨点般倾泻到基因继任者的眼睛里,以及他们的身体里。于是,一个家族的成员就带着这份福报,行走人世。
道光八年(1828),六十三岁的谭学琴因劳累过度病逝,临终前,他命家人将所有借据付之一炬,并留下遗言“我死勿令儿子废学”。他死了,但他让儿子们不要废弃学业。不废弃学业,指向的现实目标是用知识改变命运。最终这个平日乐善好施、常与读书人往来、为自己攒下名声的老人,将人生的诸般苦痛留给了他的妻子和七个子女,同时留下的,还有他一生积攒的福报。彼时,谭继洵只是一个六岁孩童,不知生死为何。父亲的猝然而逝,就像是支撑他弱小生命的一座骨架坍塌于眼前,血肉无所凭依,精神亦颓然无望。许多年后,谭继洵回忆起父亲离世时的悲惨景象,不由喟叹:“先大夫卒,同怀七人皆幼,吾母悲吾父之亡,而又念膝下茕茕无依,恒一恸昏绝,举室环哭,闻者堕泪。”在这个家庭陷入风雨飘摇之秋,谭继洵的长兄谭继升站了出来。
中国人向来有“长兄为父”的说法,年仅十三岁的谭继升虽未成年,但他责无旁贷地接过父亲留下的这副重担。他果断地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奉养母亲,照顾弟妹。他不敢忘记父亲的遗言:“我死勿令儿子废学。”他为弟妹们延请塾师教读。父亲让他们努力读书,将来获得功名。如今父亲不在了,他心疼母亲,也不忍看着弟弟妹妹们跟着受苦。他放弃学业,是为了成全弟弟们的前程。人间百味,唯苦不觉苦。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在做出那样一个决定时,内心所承受的悲怆。对少年人来说,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不只有书本知识,更多的是言传身教。父亲身上所表现出的乐于助人、救人之急的品格,深深影响了他。
在谭继洵的描述中,长兄谭继升是近乎完美之人,格局宏大,气象不俗。长兄为父这句话,在谭继升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整理家政,每天忙得精疲力竭。为了警醒自己,他在眼睛能看见的地方写上“谨身节用”四字。一个人入世太久,懂得世间丈夫最难做。世上大男人多如牛毛,伟丈夫却很稀罕。谭继升用稚嫩的双肩挑起这份沉重的家业,铢积寸累,使得孤儿寡母的家庭渐渐有了兴旺的气象。对于幼时体弱多病的谭继洵而言,哥哥谭继升犹如神一般的存在。他亲自照料生病的弟弟,四处求医问药。谭继洵后来回忆:“洵体素羸弱,兄保抱携持,体恤备至。稍长,得咳血症,兄求医调药,日夜惊扰,甚于己疾。”面对兄长夜以继日的付出,谭继洵能够回报的,是学业上的精进,而这也正是谭继升最希望看到的。谭继升、谭继洵兄弟明白,要让这个家族奋然而起,唯有在科举道路上实现突破。没有选择,便是最好的选择。
自有科举制度以来,古代中国便产生了一个功名社会。一群群儒学之士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成为不同于编户齐民的官与绅。由此分化出人的社会属性,构筑起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一个人从入泮到出仕是一条拥挤的狭路,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在这条路上蹭蹬不休。谭继升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弟弟的身上。科举之路,回报丰厚,只是过程太过漫长而痛苦。谭继洵回忆当时的情景:兄长为我找来最好的老师,给我定下最严苛的学习程式,老师偶尔外出,他则代为督课,手挟一册书卷,给我讲忠孝节义之事,娓娓不倦。我所读的唐诗,皆兄所录。遇上会试科考,兄长为我检点场具,亲自迎送。
科举入仕既成强势的主流价值观,博得功名就不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个家族的念想,这份念想深入人心。人生于天地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谭继升将自己未能实现的人生理想全都寄托在弟弟身上,希望他早日金榜题名。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三弟谭继洵聪慧过人,学业大进,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十岁时补县学附生。七年之后,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又于长沙乡试考中举人,时年二十七岁,成为浏阳谭氏宗族史上的第一个青年举子。同年考中举人的,还有湖南茶陵的谭钟麟,二人关系密切。有了举人的身份,就不用交赋税,不用服劳役,犯法后也不用受到刑罚,见到县官不用下跪,在科举之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只是还谈不上真正做官。
谭继洵迈出的每一步都得益于兄长谭继升的苦心经营,因此,谭继升在谭氏家族中享有威望。不要说他们是同胞兄弟,就算是生活在同姓同宗的村落,只要烟火相接,鸡犬相闻,也会形成同一血缘的向心力。何况,他们还是兄弟。一个人的发迹史,就是一个家族的光荣史,不仅可以光宗耀祖,其光彩更是惠及全族。反观之,一个人若是犯了王法,也会累及族人和家长。一句骇人的“诛灭九族”,便是最极端刑罚。在中国古代,九族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更是一个司法学概念。而至为酷烈的,莫过于方孝孺“夷十族”。灭十族则为朱棣的独创发明,这里包括方孝孺的学生和朋友。朱棣下令将方孝孺投入大牢,大肆抓捕其亲族朋友门生。每抓一人,都带来让他看一看。方孝孺看到他们非常难过,弟弟方孝友被杀前反劝道:“阿哥何必泪潸潸,华表柱头千载后,梦魂依旧到家山。”
我们现代人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进步心态”嘲讽方孝孺这样的人过于“愚忠”“迂腐”,但是这丝毫无损于那些古代忠良的历史地位。每个时代都有其视为不可玷污的神圣价值观,如果拿今日的价值观去衡量过去的时代,看到的自然是不可理解的愚昧。回到谭继升身上,这时候的他,只希望弟弟能够接续自己的人生理想,为家族顶门立户。待得四十年后,谭继洵仍念及兄长对他的养育之恩:“呜呼!兄之视洵如此甚笃,而洵之视兄将何以为报也!”他认为,若无兄长昔年的勤勤恳恳,以教以养,断无自己日后的荣耀加身。不负兄长不负己,是他一生志向所指。
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兄长的操持下,二十四岁的谭继洵完成了自己人生的另一件大事——结婚成家。他娶的是浏阳北乡芦烟洞国子监生徐韶春之女徐五缘。与祖上几代人的婚姻近似,谭继洵的通婚并未突破浏阳。对方是与谭家有往来的朋友。彼时,长辈的交际圈与子女的婚姻圈通常是吻合的。因婚姻关系牵连在一起的家族,像一张人为编织起来的网,将此家族与彼家族联系起来,以此壮大彼此在本地的势力。如今在芦烟村,依然流传着这样一个“姊妹易嫁”的故事:徐韶春生有二女,长女庆缘,次女五缘。庆缘经舅父说合,许配给谭家三公子谭继洵为妻。庆缘这姑娘很有心眼,对自己的终身大事非常慎重。于是,她委托弟弟借送礼之机代为调查未婚夫及其家庭情况。其弟到了谭家,发现未来的姐夫是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书呆子,并且衣冠不整、不修边幅。庆缘不愿嫁给这个邋遢的书呆子,徐家只好将婚期一推再推,最后只好由妹妹替姐出嫁。
徐氏虽然生于乡间,但她的父亲毕竟是地方上有名望的士子,与谭家联姻也算是门当户对。谭氏家族与浏阳士子之间,存在着相互需要的关系。一个新崛起的家族,在社会资源与地方秩序中的话语权仍然有限。徐氏是乡间女子,她的身上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为了帮助丈夫完成功名社会的价值追求,她日夜操劳,承担起全部家务。徐氏进入谭家后,在浏阳生了二子二女:长子嗣贻(字癸生),次子嗣襄(字泗生),长女嗣怀(怀贞),次女嗣淑(淑贞),他们便是谭嗣同的同胞兄姊。
正当谭继洵沿着人生的天梯努力向上攀登时,一场震撼王朝的风暴席卷而来。
那个像他一样参加应试的书生洪秀全,这时候刚好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落榜两次,以为上天总该眷顾他一回。可临了,还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败下阵来。洪秀全在广东花县官禄布村生活了二十三年,与绝大多数乡土社会的儒生一样,他对自己的生命起源之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尽管如此,他还是想离开这里,不为别的,那个关于富贵天降、光宗耀祖的梦境一直驱赶着他,如鬼魅缠身,如神佛附体。十九世纪中叶,一个科举失败者能够做出的选择无非以下几种:一、继续考下去,生命不止,考试不休;二、与体制决裂,比如做个黄巢;三、披发入山,做个隐士;四、返乡做个私塾先生,散淡人生。洪秀全选的是第二条道路。
落榜的洪秀全得到了那本被后世之人经常提起的《劝世良言》,这让他从一名小地方的塾师变成天父次子。1850年7月,洪秀全在花洲山人村向各地拜上帝信徒发出密令,让他们前来金田村团营。而最早来到金田村的是韦昌辉,他带来了一千多人,还有巨额的资金。他不仅提供训练场地和受训者的伙食费,连材料、燃料及其他费用都由他负担。杨秀清、萧朝贵带领紫荆山区的烧炭工人有三千多人。石达开率领的贵县客家,有四千余人。太平天国的首义诸王都成了上帝的众子,至于杨秀清以上帝之名对洪秀全进行训诫与凌辱,那是后话。
洪秀全的军队疾风骤雨般席卷中国南方,湖南站在了时代的风口。地方氏族的防御难以阻挡太平军的锋锐,各地方士绅纷纷举办团练。偶然事件就像悬于历史天空的灯盏,每一烛光亮都指向冥冥中的幽暗。咸丰帝绝对不会想到,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差,会成就湖南人曾国藩数十年的功业。有一种说法,中国古代历史上能达到圣人标准的有两个半人,即孔子和王阳明,而曾国藩算半个。可见近世之人,对这个湖南人的推崇到了何种地步。《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曾国藩这个半圣之人,虽被今人一再解读,一再误读,但面目仍不够清晰。事功者,取其功;事言者,取其言。大多数情况下,各说各话,各取所需。听上去,他们说的好像不是同一个人。
曾国藩是清廷从各省挑选出的众多官员之一。那些在地方督办团练的人员(团练大臣)大多是从前的各部侍郎、巡抚、布政使或按察使,或有类似经历的高级官员,他们致仕在湘,碰巧又在家乡居住。彼时,曾国藩正因母亲去世在家丁忧赋闲,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转来谕旨:“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张亮基)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在此之前,曾国藩已经拒绝过张亮基的邀请。他说:“国藩此时别无他求,惟愿结庐墓旁,陪母三年,以尽人子之责,以减不孝之罪。”堂堂正二品侍郎,又热孝在身,若仅因巡抚相邀,便出山办事,既有失身份,又会招致士林的嘲讽。如今皇帝的谕旨传来,他便没了退路,硬着头皮也得上。他哪里会想到,这是一条登云梯。
曾国藩与湖南绅士之间的关系,正是朝廷要利用的。在中国南部和中部地区,地方组建武装的速度正在加快。朝廷想要加以利用,又担心失去控制,便让第一流的地方绅士名流、高品级的官员加入其中,形成一个地方自保的网状系统。就在此时,谭继升组织的浏阳团练应时而生,成立不久,就与太平军发生了一场遭遇战。
洪秀全的军队进犯长沙,一支小股部队进入浏阳境内,夜抵城西北二十里的蕉溪岭下。官兵不敢出城拒敌,谭继升带领乡勇埋伏在蕉溪岭上,敲响锣鼓,点亮火把。一时间“熊熊林谷,光烂慧天”,太平军不敢靠近,只好连夜遁去。十余年间,太平军五次兵临浏阳,都无功而返。谭继升因组织团练有功而被奏保即选七品盐运使司经历,加同知衔,加保尽先选用知县。他在浏阳士绅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成为地方团绅领袖。中国人有着极重的乡情意识,湖南更不例外。凡自家居所前后方圆十余里内都称为“屋门口人”,平日即守望相助、互通有无;如遇上“屋门口人”与外乡人发生争斗,则不管是非曲直都会上前助拳,就算流血破财也在所不惜。正因如此,曾国藩才会坚定地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而他的弟弟曾国荃在用人上则完全奉行“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正如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湘军最初编练的军队,其兵都是农夫,其将都是书生。”湘军的兴起为晚清军人社会地位的凸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缘。军人化的士绅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湖南人,摇身一变,化为中兴名臣,成为晚清社会的中坚力量。无论是儒生“武士化”,还是武士“儒生化”,都是两种身份的跨界。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身份跨界,必然会导致传统社会秩序的失范和传统军事体制的更张。上至翰林,下至生员,人人喜言兵事。值得注意的是,浏阳谭氏宗族与湘军并无交集,让人难以理解。其族人跟随湘军外出征战者几乎没有,立功升官者更是罕见。谭嗣同倒是给出解释,“浏阳县于山谷间,耕植足以自存,民颇宠谨,不乐去其乡,更数世老死,不见干戈。故应募从军,视它县无十之一,而以能战博厚资大官,亦鲜有闻焉。吾谭氏又衰族,丁男始得逾二百,尤惴惴不敢远出”。谭继升兄弟与浏阳士人走得比较近,其中有欧阳中鹄、刘人熙、涂启先等。谭继洵考中举人不久,就面临太平天国起义,他没有像当时许多湘籍士子那样,选择投笔从戎,在纷乱的世道里建功立业。他还是不愿轻易放弃读书考试这条路,始终怀有一颗守护名器之心。
此后十年里,谭继洵在浏阳等地以教私馆为生,同时积极准备参加会试。咸丰九年(1859)是谭继洵一生中的重要时刻。湖南向来文风凋敝,进士、举人的录取率低于其他省份。在这种环境下,科举考试的竞争异常激烈。咸丰朝由于战乱影响,乡试屡次停科或延期,清廷出于稳定社会的目的,各省乡试增额的次数和数量都有大幅的提高。这一年三月,谭继洵赴京参加己未科会试,中贡士;次年四月补殿试,考中三甲八十六名,赐同进士出身。学习期满后,补授户部广西司主事,由此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官僚生涯。谭继洵成为京官后,即移居京城,携长子嗣贻随侍。徐夫人也于同治二年(1863)携二女一子赴京,谭家开始在北京定居下来。
我想象着,那是一个怎样的清晨,承载着一个家族数代人的梦想,谭继洵离开浏阳。街道空无一人,也没有任何照明,街道两旁堆砌着灰色的矮墙,也看不见人,让人压抑得有些透不过气来。他站在船头,透过清澈江水浮起的一层水汽,望着那座略显破败的门楼渐渐消隐于一株巨大的老树之后。水中的青天湛然无咎。上善若水,天道酬勤,勤俭无奢,淳朴如古。今日回望,总觉得那些在时间里行走的旧影,有着不为人理解的执念与执形,动摇不得。两千年来,究竟是什么力量在为谭继洵之辈点燃圣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