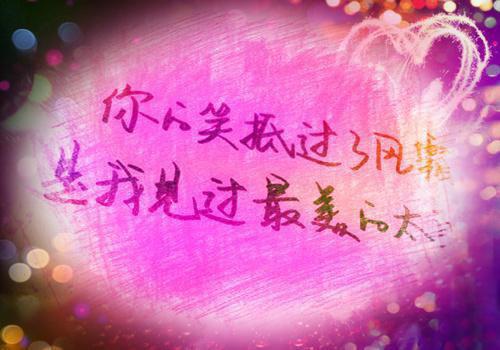东晋风流(第二部):淝水之战1.王谢家族全文免费阅读_东晋风流(第二部):淝水之战1.王谢家族最新章节
王羲之一叶扁舟,携妻儿前往会稽上任。
沿途风光十分秀丽,水中山影如虹。小舟顺波而下,如小鸟轻轻飞行在花雨中。
江水碧。
春山青。

吾心明。
王羲之宽袍大袖站在船头,望两岸繁花被春风一一拂过,如纹帐飘起,绣被波。回看舱中,爱妻正含笑望着他,心中不觉忆起纤绵往事。
那,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祖逖刘琨走后,(祖逖刘琨之事详见作者历史小说《东晋风流》。)王羲之继续住在山上向卫夫人学习书法。
罗浮山院,鹤影轻飞。
山中日月长,日月山中归。
有时他学倦了,就去山前看农夫耕田,看樵夫打柴,不然就与钓鱼童子同游花溪,捉虾放蝶,无拘无束。
若遇村姑,则与之共话。
非好其美,好其衣也——
此地女子皆善描画绣染,衣纹甚丽,王羲之以之参悟书法,多有所得。
一日,他信步走入山下村庄。
村中犬吠厌厌,日近午矣。
王羲之见村旁稻田如海,好像一张碧绿的大纸铺在大地上,真可悦也。这时一只小麻雀从田中“扑愣”而起……
忽旋飞腾,似在悬肘作书。
“它倒先在上面写字了!”王羲之大笑。
田垅上有个老婆婆坐在那里,似乎手中在忙活着什么。王羲之走过去。
老婆婆知有人来,不管,依然忙活。
王羲之轻轻走到跟前一看,哦,老太太在剪纸呢。
王羲之大乐,看她怎么剪。
老婆婆低头剪着,满头银发晃动。王羲之见她的手指干枯如树皮,却又那么灵活,大为感动。
剪着剪着,老婆婆的手指不动了。
她出神地看着远处。
远处是山,近处是田。
田中是农夫与牛儿。
农夫在犁田。
那牛甚壮甚速,“**”前奔,一路田水四溅。那农夫似乎跟不上步伐,骂骂咧咧挥鞭打牛,有些跌跌碰碰。
犁过处,田泥巴一路开花。
农夫打牛,牛儿跑得更欢了。
牛儿甩尾,那泥巴溅在了农夫衣上。农夫骂牛,一声吆喝停手歇息,左手拭汗,右手扶犁把。足微弓,踏于泥上。
此时日朗,田中泥土闪烁如黄金。
那牛悠然四望,似乎在寻觅青草。
好一幅“耕田图”!
王羲之伴着老婆婆不知不觉已凝望许久。
一人坐,一人立,望去如婆孙。
王羲之正想说什么,那老婆婆这时又从怀中掏出一张大红纸来,把剪刀一摆,眼睛只管看着眼前的景象,手中不停地“嚓嚓”剪动。那张红纸被丝丝剪开,老婆婆手握剪刀灵活地游走……
手指如枯木。
红纸如铺盖。(铺盖,被子。四川方言。)
老婆婆越剪越快,手指灵动无比,仿佛鱼儿在游泳。
王羲之见她根本不看手下剪的是什么,只管看着远方手里跟着动,便把远方景象活生生移到了一张纸上,一把剪刀随意挥剪,此中境界何其高也,王羲之非常吃惊。
这不过是一个平常的农村老太,但熟能生巧,真可谓“技进乎道矣”!
王羲之当下大悟,心中轻轻吟曰:
“心随意动,景成画成。”
那老婆婆一直没有抬起头来看他——老人家入迷了。
王羲之耐心地看她把一幅活泼泼的“农夫耕田图”剪完了,微笑离去。(一位农村老太对景剪纸,不看纸也不看剪刀,手指随意剪动,剪出来的画栩栩如生。这个故事是作者2002年1月31日在北京锦都酒楼吃饭时听唐晓渡老师讲的,今移至书中。)
后山那条孽龙久无吟声,想来已被罗浮子镇住。山中云气祥和,一切宁静。王羲之只在一个夏天的傍晚看见了异象。
那天下午他一个人正在洞经阁上纳凉,见楼下松林连竹林,苍色连碧色,十分古朴雅致,心中欢喜。
竹林的尽头有些荒草丛,葱绿蒜黄。再远些好像被雾气障住了,朦朦胧胧的,山色恍惚如镜中。
看第一眼时他并没在意。
楼下的另一边是梳海亭,亭中罗浮子与罗浮女史相坐宁静,轻声读经,卫夫人也轻立在旁翻一本书。
王羲之目力甚好,远远望去似乎正是《黄庭经》。(道教著名典籍《黄庭经》,为东晋女道士魏华存著。魏华存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女思想家与女文学家,道教茅山宗上清派祖师,世称“魏夫人”,教门尊称其为“南真”。门人有《魏夫人传》。)
王羲之知道师傅喜欢魏夫人(卫夫人当然喜欢魏夫人啦),心中微笑。
传说魏夫人写成《黄庭经》后不久即飞升而去,空余羽衣在床,何等潇洒。
想到这里,王羲之不觉仰望青空。
青空朗朗,天心似为土色。
天上云飞。
云动。
何力使然?
王羲之自然地想到:“动”字即云力也,意思是云中有力推动,古人造字,字字非虚,真何处想来。
吾之书道当如是!必与天道同耳。
望了小会儿,他又把目光漫无目标地移到地下。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对面山峰的峰顶。一松如鹤,拍羽轻飞。可能那边风很大。
从远到近,山色渐浓,草木渐清……
一石如龟,掩映在草。
一石如女,抱膝而坐。
远处云山飘渺,似三山近在咫尺。
海外又是何景?
蜃楼中可别有所居?
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此句出自屈原《天问》。)
王羲之不觉又思飘云中,渐远渐无……
这时,他忽然听到了一丝轻沉的叹息。
似深穴水响。
似春阳穿冰。
轻轻。
轻轻。
轻轻地一响,却令人好生震动。
动。
云力……
王羲之心中似有感触,不觉收回了目光——
远山退去……
近岭在前……
岩石累累……
草木云蒸霞蔚……
王羲之忽然发现,先前他看到的那片草丛的尽头与草丛对面的岩石连不起来,似乎一下子地表被什么东西隔开了。
那中间仅仅是一片云气吗?
王羲之忽悟:原来那是一处深渊。
继而他想到了那年他去后山误遇孽龙之事,心中一下子激动起来:莫非前面的深渊正是孽龙的居所?
再回看,罗浮女史与卫夫人二仙师已离去,亭中唯余罗浮子一人。
盘身而坐,瞑目颂经。
脸上似有烟气弥漫……
嗯,仙师常来此地,况且洞经阁中多藏奇经,又离深渊不远,想来方便发气镇龙。
若如此,此深渊便是彼深渊了。
刚才的那声轻响,莫非正是龙吟?
但一想又不对了,那年的路他还记得很清楚,印象中是走向了东北处的深山,应该不在此处。
刚才的那声轻响,或是幻听。师父曾说:无视无听,久之自可见色,自可闻声。
——心音也。
想到这里,王羲之笑了。哪儿就那么巧,深渊就在此处呢。
不过此楼我也来过不下几十回了,今天才发现竹林尽头的荒草外还有一处深渊,看来我尽力未健,还不够明察。
道者当如红日,一切照见。
又当如儿时梦,一切前知。
又当如孕妇,不知胎中之子。(老子曰:“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又曰:“吾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又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顺众父……”)
又如将死之人,快意辞世。
其中奥妙,虽百万言不足以尽述之。
道者无言,守玄意而映真。
……
正当王羲之心中已确定前面的深渊不是那年去过的深渊时,他看到一只在蝴蝶从一枝山花上向他飞来。
蝶。
花蝶。
花上之蝶。
这种景象每日都有,但王羲之这时却由此忽又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道理——
那蝴蝶是会飞的。
——它当然是会飞的。
先前它伏在花上,花蝶伏花枝,人不知也。
后来它轻轻飞起,翩翩在空,那可就被我看见了。
这太有意思了!
仅仅是它在飞动吗?
庄子曰:“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当它飞时,那被飞之物又在做什么?
——蝴蝶飞。
——蝴蝶在飞。
——“蝴蝶在飞”这是可以确定的,那么什么东西被蝴蝶飞呢?
——在飞,说明它有一个载体。那是什么?
——被飞,什么被蝴蝶飞?
——蝴蝶被蝴蝶飞吗?非也。空气被蝴蝶飞吗?非也。空气与蝴蝶各自飞。
——那什么东西被蝴蝶飞呢?
回答了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去解决蝴蝶为什么会飞这个问题。
蝴蝶为什么会飞?
它想飞?什么力量使它想飞?
当我想写字时,又是什么力量使我去想?去写?而一个字或一幅字写得好不好又是什么力量使然?
王羲之再次陷入了玄思中。唉,谁能破解第一推动之谜,谁就将独享大美。
庄子曰:“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见《庄子·齐物论》。)
王羲之最终明白,刚才的那声轻响就是龙吟。
不是别处龙吟,而就是后山深渊中的那条孽龙在轻声呻吟。
后山深渊非此处深渊。
然而此处深渊即是后山深渊。
何哉?渊底相连也。
事情就这么简单。
但若我不这么反复推想的话,必不能知。
现在我既知其理也,又闻其声也,那么那孽龙是否也知道了我已收到它的信息?
莫非它正要告诉我什么?
那是什么?
眼前蝴蝶已飞走……
山花合蕊,林木垂枝……
深渊之上渐渐云气浓密,若一步踏空,必堕渊底……
山色苍茫,流泉箫音。
回看日落处,云海荡漾。
云海荡漾……
云海荡漾……
云海荡漾如大笔写天书,排排耕去。
一字写下,便成云海。
王羲之并没有把他的心得告诉卫夫人。原因很简单,他不知道怎样说出来。
那就不用说吧,一些事知道就行了。
刚开始时卫夫人每天教王羲之学习书论与临帖。白天临,晚上讲。后来她渐渐发现自己讲的王羲之都懂,于是不再讲书论,只让他临帖。
诸体皆习卫家笔法,同时参习先贤。
楷书临钟繇。(钟繇,字元常,汉献帝时人,善铭石书(隶书)、章程书(楷书)、行押书(行书)三体。晋武帝司马炎建国时,曾策定文字,将钟繇、胡昭二人书法定为标准体。)
行书临刘德升、胡昭与邯郸淳。(刘德升,字君嗣,汉桓灵时人。唐人《书断》载:“(刘德升)以造行书著名。虽已草创,亦丰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钟繇、胡昭皆其弟子。刘德升被后世书家尊为“行书之祖”。邯郸淳亦汉时书家。)亦临钟繇。
草书临张芝。(张芝,字伯英,汉献帝时人。善草书,师从杜度、崔瑗。是中国第一位草书大成者。)
隶书临汉简。亦临蔡邕。(蔡邕,三国时人,工篆、隶二体。书家评之曰:“骨气洞达,爽爽有神。”)
篆书临秦碑。
甲骨临商墓。
壁书临猿人。(壁书,石壁上的简单会意、象形字。)
气书临云烟。(气书,云气的纹路。)
水书临江河。(水书,水的纹路。)
空书临鸟迹。(空书,空气的纹路。)
思书临之于大荒也……(思书,思维的纹路。)
渐渐地卫夫人发现王羲之已把所有能想到的字帖都临遍了,遂命之停习一月,任意在山上游玩。一日,王羲之告之曰:“我观古松如篆,山花如楷,月影如行,荒草如草。”
卫夫人喜极而笑:“孩子,你悟了。”
王羲之似悟非悟……
罗浮子大笑,与女史翩然乘鹤上山,望西北云气氤氲,知葛洪正与胡僧论道,其兴正酣。
卫夫人为少女时,自创书风,妩媚鲜妍而风流大度,实为古今未有之体。
王羲之习之即久,笔沾其意,一日静坐忽思佳人。
心中荒凉如泥中古镜。
久藏无晖。
只因春雨松土,透出万古清光。
乃书《野有蔓草篇》,聊寄遐想。其辞曰:
“野有蔓草,零露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字体袅袅如风筝,一丝在手,任风吹去。
言语十分谦逊。
王羲之收信时正在谢安处赏花——
谢安好花也。
见庾翼信至,王羲之请谢安为他展开读。谢安读到“过江狼狈”处,大笑曰:“若当时有我,此君必不狼狈。”
王羲之知道谢安自负,微笑视之。
读毕,谢安曰:“庾翼之意有二,一谓君书似张芝,二谓君书‘焕若神明’,亮彩非常。”王羲之笑曰:“此人不是外行,知道我学过张芝书道,只是他还不知我的书道已脱张芝之形。”
“‘焕若神明’呢?”
“我的书法当然‘焕若神明’!当年在罗浮仙山上,夫人教我学写‘一’字时,我便能领悟‘光乎日月、迅乎电驰’之意。书道若合于天,笔墨自然奕奕生辉。‘焕若神明’尚不足拟其状,今我以庄子语拟之。”
“庄子有何语?”
“庄子曰: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
“庄子此语出自何篇?”
“齐物论也。”
“庄子曰‘葆光’,老子曰‘和光’,有所别乎?”
“无所别。‘葆’为‘和’之前提,‘和’为‘保’之状态。”
“何谓和?”
“中庸曰: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达道即大道乎?”
“达道即大道也。道必达,道必大。非大不足以达,非达不足以显其大。兄还有问乎?”
“无。”
“兄莫自惹人厌烦!尔欲为陆微乎?敢向卫郎问学。”
二人谑言无间,相视大笑。
谢安又道:“君书柔媚如卫夫人,大有闺中笔意。”
“非也非也。”王羲之摇头道:“吾书柔而不媚,已脱夫人之形,已脱卫家书风。‘柔’有何不好?老子云:‘柔弱胜刚强’也。”
谢安接言道:“‘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强大居下,柔弱微细居上’。”(谢安此处所引出自《老子》通行本第七十八章。)
王羲之大笑:“我说书法,你说兵法。”
谢安亦大笑:“我修兵道,你修书道,皆为道也。当年若由我指挥赤壁之战,曹兵更惨。”
二人大笑。
王羲之又道:“当初叔父说我的字太硬了,如今正好合适。”
谢安沉吟道:“宜再修之。”
“然!”
王羲之吟曰:“笔者天也,流美者人也。”(王羲之此处所引为钟繇语。)
谢安指庭中花曰:“此花非独开,一花既放,万花芬芳。”曼声长吟:“恐鹈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王羲之见庾翼书法精工,心中也很欢喜,当下辞了谢安前往拜访,二人遂为好友,经常切磋。
不久,谢安之兄谢尚又引名士王、隐士殷浩诸人与王羲之相识。殷浩殷勤邀请王羲之到山中不住,王羲之欣然前往。
不久又有诗人孙绰前来建康找谢安、王恬下围棋,于是王羲之又结识了孙绰。
孙绰本是会稽人,性情放浪,曾作《情人碧玉歌》,情词美极,四处乐坊争相传唱。其词曰:
“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
人皆谓是淫词,王羲之独曰:“此非淫词,情词也。”
孙绰故意问:“淫词与情词有别乎?”
“当然有别。情词使人清,淫词使人浊……”
这时谢尚在旁笑道:“我偏好淫词,又如何?”
“不如何。”谢安笑曰:“如此阿兄则为水中之虫也。”
“我宁可为水虫,不愿为水精。”
说得大家都笑了。
王羲之正色道:“‘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之’。(此为孟子语。)浊有何益,不如清心以从道。”
谢尚冷笑道:“失敬失敬,原来阁下是礼教中人。”
“我当然是礼教中人!”
王羲之环视众人,大笑道:“我既放浪形骸,复又温柔敦厚,岂不更美?”
众人拜服。
是年七月十一日,王导为王羲之举行了盛大的冠礼。(本书此处写的冠礼与古礼略有出入,其义未改,曾请教于王博师。)
《礼记》云:“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
此次大典,依然由谢侯主持。
谢侯微笑,辞焉。
王导再请,谢侯固辞。
王导三请,谢侯乃不能辞也。
王导大喜问曰:“礼云:古者冠礼,筮日筮宾。(语出《礼记·冠义》。筮日筮宾,意思是选日子、定客人。筮,卜筮。古人有大事皆以卜筮而定。)不知谢侯将此大典择于何日?又请何人?”
谢侯肃然曰:“筮日所以求夫天之吉,筮宾所以择夫人之贤。不可随意为之。”
王导点头,静听谢侯谈礼。
谢侯神彩飞扬:“逸少,国之英物也,吾族子弟虽盛,唯有安石可匹之……”
王导心中甚喜:吾兄有后矣!
“故,此礼当以顶级仪式举行。上至天子、下至庶人,皆可前往观礼。孔子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非此不足以显示我中华英物之盛。”
王导微笑:“君言过矣。逸少虽不凡,不过是一童子。”
“孔子初为官时,亦是童子。”
王导不喜:“谢侯何出此言。春秋之后,谁能比孔子?”
谢鲲正色道:“不然。儒道之学希言自然,欲人成圣。君言春秋之后谁能比孔子,欲使孔子绝后乎?孔子自比周公,乃功在周公之上。今吾以逸少比孔子,非妄言也。”
“请详述之。”
“孔子之后无圣人。何哉?士人皆习孔子之道也。老子之后无圣人。何哉?士人皆习老子之道也。习其道必在道中,必不能自成一道。圣人者,自成一道之谓也。今吾观逸少书法若龙行青天,九州斯在下矣。非孔非老,自成一道,以圣人言之,有何不可!”
王导笑曰:“君言是也。不过以逸少目前的修为还不足,须痛加砥砺。”
谢鲲一笑:“丞相又错了。即为圣人之才,那么一切无改。虽然目前逸少还不是圣人,但以圣人之礼待之,宜乎!”
王导向谢鲲深深行了一礼:“君言甚美,‘于我心有戚戚焉’。”(此为孟子语。)
二人欢笑,就此议定即以王羲之的生日为举行冠礼之日。
王导又思国家新兴,不宜铺张,欲以下礼举行。
谢鲲不乐:“吾知丞相厉行节俭,然此为大典也,不可不盛。既然丞相觉得上礼太过豪奢,那就以中礼的规格举行吧。万万不可为下礼。”
王导一笑,同意了。
二人又论及谢安来,皆叹他们小字辈真真是把我们这批老头子比下去啦,甚感欣慰。
其时,大儒范宣子恰在建康,谢鲲乃前往拜见,邀为赞者。(赞者,古代举行典礼时辅助司礼者的人。《史记·秦始皇本纪》:“阙廷之死,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
范宣子喜曰:“南渡以来,吾久未见周公。今丞相与谢侯兴此盛举,老夫不敢辞。”
谢鲲故意说:“此非古礼——吾好任诞,非儒者也。”
范宣子大笑:“连你这个不是儒者的人都在行儒礼,可见大道之行也,那还有何话说。”
二人握手一笑,莫逆于心。
到了七月十一日那天,自然是风清日朗,天随人愿。
建康城万人空巷,庶民尽出,一起来看王导为王羲之举行冠礼,那个热闹劲大似卫郎当年。
因怕人多不便,王导早早地就命手下用锦幔把相府前的街侧拦了起来,分开人流。
人们只好远远地观望凝听,皆不忍离去。好事者蜂拥上前。
谢鲲正在大厅中忙碌,渐闻外面人声喧哗,知道是什么事,笑着对范宣子道:“冠礼不可缺少乡大夫、乡先生,(《礼记·冠义》云:“(冠者)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以成人见也。”挚,礼仪用物。在此用雉尾。)正好麻烦您老去邀请几位。”
“甚善。”
于是范宣子从外面请来了好几位年长者,一个个都喜滋滋地,美得不成。
范宣子心中笑骂:没见过世面的老头儿,冠礼还没举行呢,美死你!
暗窥大庭中,冠盖云集矣。
冠礼就在丞相府举行。
相府大院,自然宽敞。更喜庭中有苍松两列,翠竹万竿,郁郁青青,生机无限。
王导指眼前青松,对皇帝司马睿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初来江南时,臣觉此松身影孤单,今日视之,分明又是一棵大夫松。”
司马睿亦笑:“丞相家多出大夫,此松自然是大夫松。”
心中却想:王家人果然有纂位之心!那大夫松乃是秦皇泰山封禅时封下的,老家伙自比秦皇,居心叵测!
王导哪知其心思,忙着向司马睿父子介绍来宾。
众人纷纷向司马睿叩安,私下皆曰:“为何还不见逸少出来?”
来客中有几位是从山东老家来的,都很久很久没看见王羲之了,忍不住不停地问王导冠礼为何还不举行?
王导含笑一一答之:“就快好了。”
人们渐渐清静下来,看谢鲲布置。
其实在客人来之前谢鲲早就把场地布置完美,如今根据临时情况又略作修饰,更觉华美整洁,恢宏大气。
凡为礼,必整洁一新。
古礼:童子之冠礼当在阼上举行。
阼音作,大堂前面向东的台阶。
之所以向东,取向阳之意。
之所以在阼上举行而不是在高台上举行,《礼记》注曰:适子也。
适子,意谓符合童子天性。
童子惧上高台,又好在台阶上玩耍,故将冠礼设于阼上。古圣设礼,取之于日常生活,本之人性也。
中华礼义之精,由此可见。
辰时,王羲之出。
衣白袍,散发如古人。
身旁伴者卫夫人,居其母位。身后一溜儿年长之妇盛妆相伴。
见王羲之气象万千,众人耸动。
王羲之缓缓走到阼前,轻轻止步,笑视王导。
王导笑视谢鲲。
谢鲲轻咳了一声,与范宣子联袂而出,身后皆一溜儿礼官,躬身在后。
二人表情渐凝重,肃然无语。
趋进,翼如也。(语出《论语·乡党》。)
王导大悦。
司马睿亦暗自点头。
但闻谢鲲唱曰:“乐起——”
于是乎丝竹悠扬,钟鼓震荡。乐曲甚美,余音袅袅,绕梁欲飞。
众人大悦。
乐止,谢鲲唱曰:“童子出——”
王羲之这时已经出来了,听了谢鲲这话有些不知所措,急忙看着身旁的卫夫人。
夫人轻声道:“你再往前走两步就是了。”
王羲之于是再移玉趾,白袍飘飘。
列中有客见王羲之应变得体,轻声赞曰: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命!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命!”(此诗为《诗经·国风·麟之趾》。)
观者皆叹王羲之沉稳有度,大似王导。
谢鲲与范宣子相视甚悦,一齐洪声唱曰:“童子即出,请延宾客——”
于是王羲之向阶下宾客三拜而谢。
宾客皆受而不答,盖此时王羲之还未加冠,依然是一童子。
王羲之拜毕,悠然静立。
亭亭似青松。
谢鲲又唱曰:“宾客各归其位——”
于是阶下众人按君臣、尊卑、文武纷纷入座。王导与司马睿父子同席,王敦与郗鉴等武臣同席。
王敦问郗鉴:“此子如何?”
郗鉴似乎艳羡不已:“好个儿郎!”
王敦大笑。
王导见其无礼,目之。
王敦最惧王导,当下“吧答”,嘴巴闭上了。
王羲之即践阼,谢鲲唱曰:“童子践阼,请备冠——”
于是阼上礼官、长妇皆退,只余谢鲲、范宣子与卫夫人三人伴于王羲之身旁。
下面司马睿问王导:“为何当初朕行冠礼时,不如此时隆重?”
王导笑道:“陛下行冠礼时犹在中原,那时老臣幸亦在场,忝居末位——先帝甚爱陛下,以太子礼为之,过于比时百倍也。”
司马睿那时还小,这会儿恍恍惚惚记不清楚,听王导说得隆重,满意地笑了。
座中桓彝闻此言,心中大骂王导虚伪:
明明那时先帝只以二等王子看司马睿,老家伙却说“以太子礼”;明明当时在打仗,冠礼草草举行,一会儿就收场了,哪及此时悠闲隆重?老家伙当面撒谎不脸红,欺我不知乎?
桓彝当下笑吟吟地看着王导,王导只装不知。
这时阼上谢鲲唱曰:“冠至矣——”
礼官们躬身捧冠而上。
长妇们亦复上,将王羲之左右围绕。
王羲之这时不觉有些眼花缭乱,看见那底下谢安、孙绰等好朋友们正在望着他笑呢,忍不住嘴角也露出了一丝微笑……
卫夫人察之,暗牵其袖。王羲之好不容易忍住了笑,乖乖地站在那儿,干脆任大家摆布。
只听得谢鲲又唱曰:“请童子之父上前,为童子加冠——”
王导面带微笑,缓缓而出。
因为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很多年前已在上党之役死于国难,故此时王导以叔代父,为王羲之着冠。
王羲之见王导一步一步向自己走来,恍如父亲当年,忽然泪下。
那时:
每次父亲从外面回家,我就会远远看见他的身影。
父亲很矮,父亲很胖。但父亲在我眼中是一位威严的父亲。
威严的父亲慢慢向我走近,就变成了慈祥的父亲。
一步一步,父亲的身影放大。
一步一步,父亲将我拥抱在怀。
“父亲!”
再后来父亲走了,我每天在家里和母亲一起等父亲回来。
母亲在家里缝了春衣缝夏衣,缝了秋衣缝冬衣,可是父亲没回来……
我在家里天天练字,天天洗笔,不知不觉门前的那口小池塘的水由清变蓝,又慢慢地变黑了,父亲还是没回来……
想到这里,王羲之心中悲苦,泪珠滚落。
座中宾客见他刚才还好好的,忽然哭了起来,都十分惊讶。
王敦哈哈一笑:“小孩子啦不是?哭得像个女孩子似的,成何体统。”
郗鉴曰:“此子思父,大将军莫嘲之。”
王敦点头,遂不再笑。
王导知道王羲之想起了父亲,心中暗叹,轻轻上前道:
“逸少!今你成人矣。愚叔希望你今后有成,以慰你父亲在天之灵。”
王羲之心中激动,望着王导汩汩泪下。
王导深深叹息:“孩子,想哭就哭吧。”
于是王羲之在这隆重的冠礼之上,当着众人的面大哭一场。
众人皆伤感。
卫夫人站在王羲之的一旁为他拭泪,心中亦甚是凄然!
王羲之渐渐止住了哭泣,心中想到:一切都已过去,如今我也成人了,该做自己的事业。大家都如此关心我,不可以再感伤。
于是止泪曰:“请叔父为我着冠。”
一泣一止间,不觉声如龙吟矣,雄浑悠长。
王导点头:“好。”目视谢鲲。
刚才王羲之的这一哭,谢鲲、范宣子二人也很感动,心中皆叹息:古来圣人皆重情也……互相交流赞许的眼神。
王导见谢鲲这个主持人还在发呆,只好又提醒道:“谢大人!谢大人!”
谢鲲如梦初醒,宏声唱曰:“着冠——”
于是王导从礼官手中接过冠来,轻轻地戴在了王羲之的头上。覆之,定之,抚之,顺之。望去王羲之头戴新冠,长身玉立,脱童子之形矣。
众人喝彩。
定眼望去,王羲之穆然静立,落落大方;王导举手投足之间莫不从容,皆叹王氏家风如此大气,非一日养成。
冠毕,大宴宾客。
王羲之先敬王导,王导代其父饮之。
王羲之再敬卫夫人,卫夫人代其母饮之。
三人其乐融融,望去真如一家人一般,又有谁知其为孤子。
父母敬毕,王羲之言词恳切,举杯谢客,风度翩然。
众人大悦。
王羲之最后举杯答谢乡大夫、乡先生,诸老争相饮酒,不觉陶然大醉。
范宣子唱曰:“请皇上赐礼——”
司马睿乃赐王羲之黄金百两,珍宝无数。
王导率王羲之拜谢皇恩。
王羲之见司马睿粗俗,心里不喜欢。碍于叔父颜面,勉强下跪。
最后乐声再起,冠礼成矣。
众宾客辞去,王羲之挥手谢客。
翩翩玉树,庭前临风。
衣冠似冰雪,清朗无尘。
范宣子与谢鲲私下论曰:“逸少大有龙凤之姿。”
谢鲲曰不然:“此非龙凤之姿,乃圣人之象也。‘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语出《老子》第四章。象帝之先,好像是人间帝王的祖先。)
范宣子咋舌,微笑着摇头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