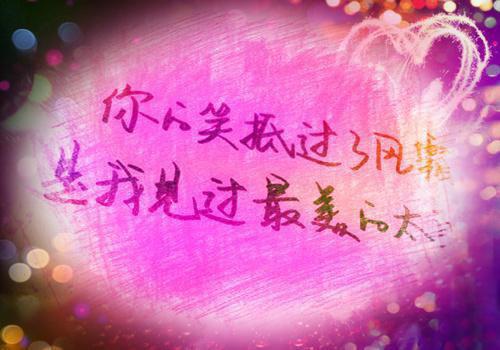海明威文集全文免费阅读_海明威文集最新章节
导读
厄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年)是美国最享盛名的现代小说家。1899年7月21日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一个医生家庭。父亲热衷于打猎和钓鱼;母亲爱好音乐和艺术。他们的爱好给了海明威很大影响。海明威一方面继承了父亲爱冒险的精神;一方面又受到了母亲艺术天份的影响。1917年中学毕业后当见习记者,接受了新闻记者的严格训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志愿入伍,参加了美国医疗队。1918年他在意大利前线受重伤。战后住在巴黎,当了《多伦多明星日报》的驻外记者,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他的作品语言简练,内容深刻,形成了独到的风格。1946年他的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出版。小说描写一群参加过欧洲大战的青年流落在巴黎的情景。他们精神苦闷,情绪彷徨空虚,引起了战后不少青年的共鸣,被称为“迷惘的一代”。小说因此成为“迷惘一代”的代表作。海明威也因此成为“迷惘一代”的代表作家。
二十年代末海明威回到美国,居住在佛罗里达州。他广泛地游历:去西班牙看斗牛,去非洲打猎,去古巴钓鱼。写出了不少以斗牛士、猎手、渔夫为主人公的作品,创造了有名的“硬汉性格”。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作为战地记者四次去西班牙。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海明威又一次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到了欧洲,参加了不少军事行动,写出不少战地报道、反战题材的小说和剧本。

1941年3月,海明威以纽约《午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在重庆秘密会见了**领导人周恩来。对于抗日战争的采访,他写出了六篇文章发表在《午报》上。
1945年二战结束后,海明威定居古巴。1952年发表优秀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再次引起轰动。《老人与海》发表两年后,海明威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老年的海明威病魔缠身,1961年7月2日用猎枪在自己的寓所自杀。他独特的艺术境界、勇敢不屈的“硬汉精神”永远存在于世界文坛之林。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独特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其中“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名言激励了很多克服困难的人。小说取材于1935年前后,是海明威居住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岛期间,从哈瓦那海湾渔民的交谈中听到的,当时发表在杂志上,只有200多字。《老人与海》的问世,是在16年以后的1952年。
故事的主人公是古巴老渔民桑提亚哥,他已经有84天没有打到鱼了。头40天,一个孩子很佩服他的本事,跟着他出海学打鱼,结果一无所获。他的爸爸妈妈说老头倒了运,不再让他去,孩子搭上别人的船,头一星期就打到三条鱼。他看见老头每天空着渔船回来,心里很难过。到了第85天的早晨,孩子拿着沙丁鱼和鱼食送他出海,祝他好运。钓丝动了,一条马林鱼在晃动,他目测了一下说:“它比小船还长两英尺呢。”鱼一直拖着小船走了两天。第三天,老人拿出当年的威风,忍着伤痛用鱼叉扎死了这条大鱼,把它捆在船边。死鱼的血招来了鲨鱼群,它们大口大口地吃着马林鱼的肉。老人用绑在浆上的小刀子、用鱼叉、用棍子一次又一次地劈打着鲨鱼。他坚定地高喊着:“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最后,一条鲨鱼朝死鱼的头上扑来时,他知道一切都完了,他失败了。
《老人与海》倾注了海明威近四十年的创作风格。孤独的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乐观自信勇敢无畏的性格、深藏内心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是作者精神世界的体现。情景交融、准确生动的动作描写,娓娓道来的叙述,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老人与海》作品的表达方式是从感觉、视觉、触觉层层递进展开的。这样写能够使作品节奏性强,线条清晰,拉近了作者、读者和主人公的距离。
1929年海明威著名的反战小说《永别了,武器》出版。它给海明威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小说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美国青年亨利在意大利救护队担任上尉。在一次进攻前夕,结识了英国姑娘凯瑟琳。凯瑟琳的未婚夫在一次战役中阵亡了,因此,生命对她来说更为珍贵。她希望亨利能平安地回来。在前线,亨利的腿被炸伤,送进了米兰的一所医院。在凯瑟琳的细心照顾下,亨利逐渐痊愈。他们相爱了,并准备战争结束后组成家庭。就在亨利准备重返前线的前夕,凯瑟琳告诉他她怀孕了。前线战事越来越糟,每天都有阵亡的危险,他厌恶战争,决定逃跑寻找凯瑟琳。历经磨难,他和凯瑟琳逃到了中立国瑞士,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等待凯瑟琳的分娩。不料,凯瑟琳和孩子都死于难产。
《永别了,武器》倾注了海明威全部的思想感情。小说中的亨利代表了一大群单纯、富有激情的青年。他们听信了政府的宣传,到欧洲战场充当了炮灰。残酷的没完没了的战争,使他们感到厌倦,他们终于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世界杀死最善良的人、最和气的人、最勇敢的人”,这就是他们的觉醒。凯瑟琳的原型,是海明威在美国医疗队结识的初恋情人艾格丽丝。他给予了她最美丽、最勇敢、最温柔、最贤惠的性格。她细心地照顾受伤的亨利;她怀着孩子,在大雨中和亨利一起逃跑;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她还安慰亨利:“好的,我会夜夜陪你的。”这是一部爱情的悲剧小说。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贯穿了全书,尽管他们在瑞士有过一段平静的生活,但战争造成的伤害,在人物最后的命运中结束。小说从个人幸福的角度谴责了战争。因此,这部书一出版,就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