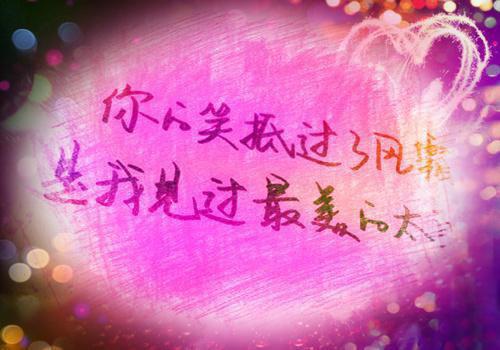买办之家全文免费阅读_买办之家最新章节
余隆泰筑桥的善举把上苍感动了
余姓人家的日月发旺,吉星高照,那是从余隆泰大人在他外的子牙河上,修筑了一座五槐桥开始的。
那时节,余隆泰刚刚五十岁,和他的亲兄弟几个开的皮货、绸缎庄生意做得好不兴隆。父辈留下的老宅院住不下了,余隆泰便在河沿边买了八亩地,四角奠基,掘地三尺,又请了和尚、道人设经堂、道场,驱散了那地面上原来的妖气、穷气、野气,又恭祈土地老爷护佑平安,这才破土动工。一年的时间盖起了一座大宅院,青砖对缝,飞檐交错,果然好一派风光。
由此,余隆泰举家迁入新居。彼时,他已经有了五子一女,一家人尊老怜幼,父父子子,兄兄弟梯,真是享不尽的天伦之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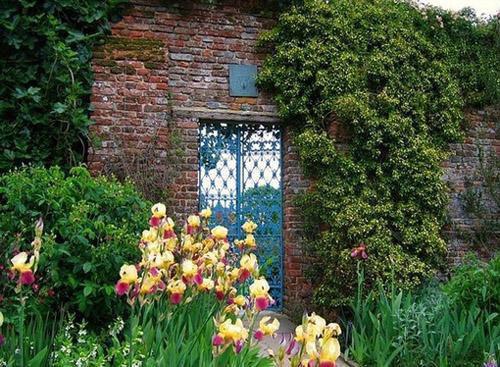
只是,就在余家新府邸对面,流水潺潺地横着一条大河,河面上船来船去,帆影翩翩,倒也堪称是美景怡人。谁料,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位道人,他在余家府邸邸门前左顾右盼,足足观察了大半天时间,最后将一纸黄符贴在门上,然后便扬长而去。
余隆泰不懂符文,便揭下这张符纸,带在身边,找到观里向道士请教。那道士如此这般地一番开导,最后,余隆泰先生明白了,如今余隆泰一家虽吉星高照,但门前一条大河挡住了家运;而余氏人家要想永葆万世富贵平安,就必须在河面上筑一座大桥。
筑桥,算不得是什么难事,余隆泰有钱,莫说是飞跨大河西东,就是飞跨半个天津卫,余隆泰都掏得起。马上找包工头,余隆泰力主维新,你还别给我搭什么木桥、石桥地对付,造福一方,功及子孙,洋人在海河上架起了万国大铁桥,成了天津一景,你也给我在余家府邸门前筑一座西式的洋桥。桥当中可走大马车,能过“四轮电”,什么大轿子马车,还有洋人的新式小汽车,都能从桥上过,车道的两侧再筑上行人边桥、铁栏杆、铁扶手,桥上挂着电灯泡,要的是新式、洋派。
请来日本桥梁工程师,画了几十张图纸,什么结构图、平面图、展开图,余隆泰一概看不懂。只有一张立体图,和西洋油画一样,一座大钢桥,桥上车水马龙、行人不绝,桥下大河流水,水上有渔船往返穿梭。“好!,余隆泰大人挥手在书案上拍了一下,立即破土动工。开工的第一天,余隆泰大人带着自己的五个儿子,每人在大桥的奠基石上培了几铲土,随之,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子牙河两岸的民众向余姓人家致礼感谢,浩浩荡荡,兴师动众,一项大工程便由此开始了。
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大桥筑好了,请来风水先生,请来道士、高僧,又请来相士大师,众位神仙一一推算,英雄所见略同,全选定了十月初八这个吉日。余隆泰大人一听,当即又挥手在书案上拍了一下,“着呀,十月初八恰正是我的生日,选在这一天开桥通路,真是大吉大喜呀!于是,就在余隆泰先生五十大寿的这一天,大桥落成通行,那一番热闹,真成了天津卫百年来的一大盛事了。
早在半个月之前,大桥两端便搭起了彩楼,青松翠柏,把桥头的彩楼装点得好不气派;彩楼中央,意国电灯作为贺礼送来的五彩灯泡,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轮着番儿地一阵
明一陈灭,把天津老少爷们儿看得眼花缭乱。由大桥下坡,直到余家府邸大门门,新筑了一条大道,清水洒街,黄土铺路,把八面的来风和四方的福禧宏运,一起引向余家大院。好风水,好排场,余姓人家就因筑了这座大桥,这百年的荣华富贵,就要受用不尽了。
因为余隆泰大人在子牙河上筑了一座大桥。天津卫的宿儒士绅联名在天津的《庸报》登了一个整版的贺刊,贺刊中央四个大字:“一人有庆”。表面上是说余隆泰为民筑桥,虽然造福四方,但却是一人的庆事;但是典籍上有据:“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久。”所以这“一人有庆”四个大字,才更是对余隆泰大人造福乡里的歌功颂德。
光在报上登了贺刊,还不足以表示民众对余隆泰的感激之情,子牙河两岸上万户人家还给余家挂了善人匾。挂匾,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大事。中国人,凡是大户,名门望族,大门上若是不挂上几块匾,那就象一个人不穿衣服一样,压根就见不得人。所以,中国人只要一有了光彩的事,立即便要挂匾。考中了状元,朝廷给挂匾:“状元府第”,那是至高无尚的荣誉;做了官,百姓给挂匾:“佑我黎民”,一是颂扬父母官的功德,二也是暗示大老爷对百姓要手下留情。有过一个笑话,说是一个官员离职而去的时候,百姓给他送了一块匾,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天高三尺”,中国式的幽默。可见中国人把匾看作是对功过的评价。
子牙河两岸百姓给余府挂的匾,上面的四个字很俗:“积善人家”也是求其通俗易懂,典出于《易经》,“积善人家,必有余庆”,是说余隆泰做了善事,他的子孙后辈就必有好日子过。
余隆泰家挂了善人匾,百姓们心里还觉着欠他的情,于是 又八方筹措,就在余隆泰家府邸门外,民众又给余家筑了一座 善人牌坊。立牌坊,那就更不得了了,中国的牌坊有许多种,而 主要的却只有三类。一是圣人牌坊,那是只给圣人们立的,一 般的状元,够不上“份儿”;第二类是贞节牌坊,是给贞女烈妇 们立的,当然其中个别的也立错了,但中国人尊重既成事实,也 就算了。第三类牌坊,就是善人牌坊,数额有限,不可滥立,一个天津卫,门外立下善人牌坊的;余隆泰家是第四户。
一切准备就绪,十月初八,余隆泰过生日,大桥通行,子牙河两岸一派节日气象——
只是,这座大桥叫什么名呢?论这座大桥的势派、结构,仅次于横跨海河的万国大铁桥,而天津卫任何一条河上每一座铁桥、木桥,以至于浮桥,一律按“金”字排名,金钢桥、金汤矫、金钟桥……等等等等。偏偏,余隆泰大人的命相属木,金克木,余隆泰腻歪这个金。为此余隆泰家资万贯,自己却不带一件金器,一家人上上下下也一律不许有金饰品,女子可以佩玉、戴翠,无论什么猫眼、祖母绿都不为珍贵,只是这个金字,万不可让余隆泰听见,更不许让他看见金活。
那,余隆泰大人修筑的这座桥叫什么桥呢?有人提议叫善人桥,余隆泰修路筑桥造福一方,功及子孙,子牙河两岸万千黎民又于通桥之前给余家挂了善人匾,称这座新桥为善人桥,当之无愧。但余隆泰大人不同意,他说,修路筑桥本来就是兼善天下的事,做了善事却又要人人每日感恩戴德地颂扬善举,其用心虽好,却又变成了伪善,行善而不言善,方为真善,所以这“善人桥”的名字是万万不可取的。还有人说,索性就叫隆泰桥,留芳百世,扬名天下,天下人尽知有隆泰桥,隆泰二字被万民口诵心传,岂不也是为人一世的大幸。但余隆泰仍不以然,他说桥上人多车多,免不了日久天长会有点什么灾祸,倘一位什么人在桥上跌倒了,弄了一身泥巴,别人问及他何以如此狼狈,他必会顺口便答:“还不就是那座倒霉的隆泰桥!”那时,这隆泰二字岂不又任人唾骂了吗?再说,桥总有漏有塌,多少年后人们说及隆泰塌了,隆泰漏了,隆泰歪了,隆泰邪了,算了吧!别如此由人笑骂了。
真是愁煞人了,桥,总要有个名字吧,余隆泰冥思苦想,甚至不惜重金要奖赏能为这座大桥起出桥名的各位贤达。于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人们从四面八方给余隆泰寄来了自己想出的桥名,什么留芳桥、济世桥、思泽桥、正阳桥、昆桥、鹏桥、甲木桥,等等等等。
“余大人,你快出去瞧瞧吧,天神显灵啦!”忽然一天早晨,余氏府邸的仆佣头人吴三代匆匆跑来向余隆泰禀报说门外出了一桩奇事,余隆泰末及详问,立即披衣出来,推开院门,立在高高的石阶上,举目向不远处的子牙河望去。果然,地现异相,余隆泰筑桥的善举把上苍感动了。
五株高大的槐树挺拔英武地树立在新桥的两侧,左为二,右为三,枝叶繁茂,树干粗壮,斑剥的树皮,看上去少说也有百年的树龄,高大的树身,树根处盘根交错,看上去至少也要在这里长了几十年。明明是从天而降的五株古槐呀,昨天黄昏河岸还是一片秃秃光光,莫说是参天古树,就是连根树苗都没有,说是有什么人趁夜间栽下的这些古槐,何以树根处不见新土?
“苍天明鉴,赐福余姓人家!”看着一夜之间突然长出来的五株古槐,余隆泰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设坛、上供、焚香、礼拜,余隆泰率五个儿子和男性佣人一齐向五株古槐叩拜,当即,余隆泰大人便发下话来:“这座桥就叫五槐桥吧!”
由此,天津卫多了一座五槐桥,而五槐桥又系余姓人家出资修筑,于是,天津人才将五槐桥称为是余家的五槐桥,而又将修筑了五槐桥的余姓人家,称之为是五槐桥余家。
余隆泰筑五槐桥造福津门故里七十二沽黎民,子牙河上的一座五槐桥,也给余隆泰一家人带来了兴旺的好日月。一座五槐桥,使余隆泰从一个富商而变成了贤达名士,不消几多时间,余隆泰在天津卫的名声,可是比五槐桥的名声要大多了。
这样,就看出余隆泰的心计来了。在子牙河上筑一座桥,才几个钱?几十万两银子罢了。这些银子放在家里,老银子不会生小银子,旧银子不会生新银子,多不过放进票号去生些利息,余隆泰又不稀罕多那几个钱。
但是,这几十万两银子用在子牙河上,明着看是余家给百姓们筑了一座桥;其实,是桥上过往的行人车马给余隆泰扬了名。扬了名,有什么用处?扬了名,余隆泰就不再只是一名被读书人看不起的商贾了;扬了名,余隆泰就成了天津名流,他就有资格结识宿儒名士,他就被官府请去奉为上宾了。筑了这座桥,余隆泰就从一个“买卖人”变成有头有脸的人物了。所以,这五槐桥,其实是余隆泰为自己筑的一个跳板,一个要跻身于显赫人物的跳板。
果不其然,自从筑了五槐桥,余隆泰的身价真就一天天地升上来了。直到最后,他作上了三井洋行中国掌柜,既是一位民间人士,又有官商的身份,他已能出入直隶总督府、天津府衙门,与总督大人和道台阁僚们称兄道弟,平起平坐,余隆泰明明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李鸿章连连击掌,为余隆泰鼓劲
追溯余隆泰何以平步青云,一跃而成为天津的首席买办,这还要从李鸿章大人在天津办洋务的事说起。
李鸿章原籍安徽合肥,入仕之后,人们称他为李合肥,有一首诗中的一句名言:“宰相合肥天下瘦”,指的就是李鸿章为朝廷效忠多年,做了宰相,肥了自己,苦了百姓。
公元1870年,同治九年,李鸿章奉命到津,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此,他做了封疆大臣,且兼与盘据北方的列国势力周旋。李鸿章到天律后,大刀阔斧地大办洋务,不到几年时间,便把个天津城折腾成了一个热火朝天的集工商、金融、铁路、邮政于一地的重埠。
李鸿章在天津办洋务,有人说是受了洋人的撺掇,这固然也是对李鸿章的一种贬斥,不过哩,凭李鸿章一个老官,而且是一个到外国晋见人家皇帝,在皇宫里随地吐痰的昏聩官僚,说他会突发奇想,要推动中国建立西方工业生产体制,未免也是对他过于颂扬了。李鸿章办洋务,是他亲自吃过洋人的苦,几次出使西洋,虽说身为大清国的重臣,但人家却只将你视为是求和的败将,连宴席上的座位,都将你排在下位,明明是要当众不给你面子。这时,李鸿章也许会想,以大清国的幅员,倘每人手中也有一把洋枪,凭你们这些弹丸之地的小国,几百万人口,哪里是大清国的对手?
洋人么,自然很鬼,他们先用大炮兵舰攻破你的大门,让你作了败将;然后又引诱你学他们制造大炮兵舰,兴办洋务,将他们攻打你的武器再卖给你,这才是将你牢牢地拴在他们的车辕上,乖乖地由他摆布。
大清国的洋务运动,始于扬言创立海军之时。那时,停泊在中国海域的英军九十九团,有一个名叫马格布的军医,他将船上的几个工匠带下来,找个地方利用些旧车床造出来了一些火药、子弹,算是开办了一个工厂。李鸿章听说洋人要帮助朝廷造军火,自然十分高兴,立即就批了一块地皮,让这位马格布在中国推行洋务。马格布受宠苦惊,马上到船上把“水上修理厂”的机器拆下来,在他的工厂里布置好。并请李鸿章大人来厂参观。事后,一位当事人回忆彼时彼际的情形,写了一本书,书中写道:“这位统帅(指李鸿章)到那时为止,除了看过乡下脚蹬的浇田用的挂链水车以外,恐怕还没有见过任何更复杂的机器。如果告诉他这是属于他所感到头痛的李泰国舰队的,劝他购下,那是毫无希望的。现在,这个对机器本来就很陌生的人,看到它忽然灵活地动了起来,发生的惊奇是戏剧性的,一切疑虑和踌躇都消失了……”
中国的事,就是这样有趣,发动了一场洋务运动的人,竟然是一个对“洋务”一无所知的人。这个人在天津大办机器局,拨出白银八万两,向英国购买来制造“火药铜帽”(子弹)的成套机器,而被他从英国请来建立机器厂的,又并不是什么工程师,而是一个当年曾经在曾国藩的阁僚中充任“剃头”队长的英国武夫戈登。反正是一个要花钱办洋务,另一个是要以协理办洋务发财,情投意合,这天津机器局就建立起来,而且不到几年时间,就有了大发展了。
公元1886年,光绪十二年五月,朝廷派海军大臣醇亲王奕摄来天津巡视北洋海防,李鸿章便带着这位亲王到天津机器局参观。据后来的一部《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记载:天津机器局“局有八厂,共屋百余间,环于海光寺外,匠徒七百余名,每日可造哈乞开司枪子万粒,嗜士得枪子五千粒,其余炮车、开花子弹、电线、电箱及军中所用洋鼓吹,皆能仿制。……时伏水雷九具,于寺外积潦中一一试放。雷中装火药四十八磅者,水飞十余丈;装火药八磅者,水飞五六丈。盛杏孙观察复觅电光灯,织布机器两事设于局中,并请王试观。”当然令老王爷大开眼界。于是,“王与爵相,善都统坐铁轮车流览各厂,工人照常执业不掇。”
一部《巡阅日记》没有记载下醇亲王于巡阅天津机器局之后,留下了什么“垂训”,他大概也就是“大悦”罢了。操办洋务的人对于办洋务是外行.巡阅洋务的人,对洋务该更是闻所未闻了。好在,能让他们知道西洋机器就是比中国的打铁作坊强,也就足矣了,此外,还要于他们有什么苛求呢?
李鸿章于天津办了机器局,随之又操办了开平矿务局,李鸿章雇用英国人巴赖为矿师,又从英国买来开矿机器,于是便在距天津200余里的开平,开了一座煤矿,这就是后来的开滦煤矿。开平煤矿于公元1881年,光绪七年出煤,“所出煤助,极为精美,可与洋煤并驾齐驱,价值既廉,销路又广。”一下子,使北方成了一个产煤的富地。
开了机器局,办了煤矿,又相继办了邮政、电报等等“洋务”实业,随之,顺理成章,李鸿章便要修筑铁路了。只是,修铁路,谈何容易,就在开平煤矿出煤的1881年,英国人出钱修了一条从唐山到胥各庄的全长11公里的运煤铁路。但是,修路的英国人万万没有想到,运行在这条铁路上的蒸汽机车,夜深人静,一声汽笛长鸣,竞把毗邻于唐山、胥各庄的皇家东陵的守陵官员从睡梦中惊醒了。立即,一声令下,全体守护皇帝陵墓的官兵全副披挂四处查访,一定要把那个发出怪声的刁民捉来问罪,因为制造怪产事小,惊动了地下的皇帝寝陵事大,你是存心不让老主子在地下安息怎么的?查访了一夜,终于有了 结果,原来惊陵的怪响非刁民所致,这原是邻近的煤矿上新通 了一种火车,而那吓人的怪声则就是这种火车的汽笛声也。
飞马晋京,立即向朝廷报告,十万火急。“近有西人于皇陵左近修筑铁路,其路上行驶之机器火车啸声震岳,致使列祖列宗地下寝陵不得安宁。”这还了得,中国这么大,老皇上死了都没个安静地方长眠,洋人也太放肆了。刻不容缓,朝廷立即派下官员,星夜赶到开平煤矿。“圣旨”,开平铁路不得行驶机器火车。
只是,不让矿上的火车运行,那煤矿不就停产了吗?英国人没有办法,只得在火车前面套上几百匹骏马,几十个人同时挥鞭策赶,这便给天下人留下了一个马拉火车的大笑柄。
办洋务,没有铁路不行,而李鸿章要想筑路,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洋人蹿掇李鸿章修铁路,又重演了英国人马格布的办法,用实地表演打动李鸿章的心。
那一年是公元1885年,光绪十一年,李鸿章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而刚刚跻身为天津名流的余隆泰只有50岁年纪。一天下午,余隆泰接到一件帖子,请余隆泰大人赴紫竹林巡阅机器火车表演,邀请人是天津怡和洋行的英国董事长。
紫竹林,地处天津城区的东北方向,好大一片空地,怡和洋行为了让李鸿章和中国商人们看看火车的神威,从英国运来了各种器材,在紫竹林空地上铺了一条五公里长的小铁路。铁路铺成之后,恰和洋行又从英国运来了一辆火车,当场操作,他们选定了一个日子,要请李鸿章、中国官员和天津、北京一带的名流、富绅、宿儒、巨贾们亲自乘坐一次他们的机器火车,以萌醒中国人对修路的渴求。
坐着怡和洋行的机器火车,在紫竹林旷野上转了一圈儿,一个钟头之后,李鸿章率领总督府和天津的地方官员,以及一起来参观乘坐火车的天津士绅富贾,回到了直隶总督府,说是用茶小憩,其实是鼓动天津商界向朝廷里的老朽们施加压力,提出修筑铁路的奏折。
天津商人们自然知道,近几年来,朝廷向欧美派出的使臣们,回国之后,大多向皇帝呈报过欧美列国因经营铁路而促成国家兴旺的情形,而李鸿章又是于修筑铁路最为热心的一个,他曾提出了修筑铁路“大利九端”的说法。但是,李鸿章修筑铁路的主张,不仅遭到了王爷老臣们的极力反对,就连许多读书人也认为修筑铁路实为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行径。反对修筑铁路的人说铁路有四害,其一便是资敌。他们说,如今列强野心勃勃,觊觎天朝,而我大清帝国所以还能巍然如泰山,就是因为内陆没有铁路。因此,列强虽有坚炮利舰,但他等若想发兵进京,千里迢迢,那还是够他们走一阵子的。利用这一阵子时间,京城贵胃,或迁家、或转运细软,也都还来得及;倘有了铁路,敌兵朝发而夕至,我等还来得及逃跑吗?此外呢?那些老朽官员们还提出,修筑铁路扰民、失业、夺民生计,等等等等,那是万万不可为的!
何况,朝廷里极力反对修路的,不是别人,正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酵亲王奕摄。
李鸿章孤掌难鸣,在朝廷里不能说服守旧派官员们修筑铁路。于是,他就想在天津汇集商界力量,先把铁路修通了,再迫使旧派的官员们承认事实。
李鸿章当然知道,天津商贾虽然不问朝政,但自开埠通商以来,天津百业兴旺,一场洋务运动,又把天津变成了一个大商埠,如今的天津商人们早就对内陆的交通状况不满了。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渤海之滨,万国的商船可以直接沿海河驶进天津,可是洋货到了天津,要靠马车运往西北内地,而外商要买的货物,也全是靠大车运来。这一出一进,停滞缓慢,眼望着白花花的银子,就是装不进自己的腰包。前不久听说唐山至胥各庄修了铁路,如今又有英商把铁路铺在天津城郊,请富绅巨贾亲身体验一下近代交通的便利,天津商人自然就开始躁动了。
李鸿章当然鬼得很,他决不会在修路问题上和皇上的老爹作对。直隶总督府的大花厅里,众目睽睽之下,他更不会公开鼓动天津商人与朝廷作对。东拉西扯地一面和天津商人们说些闲话,李鸿章一面王顾左右而言他地只说些铁路的好处。
“我们中国人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座的诸位贤达之中,我就听阁僚们对我说过,其中很是不乏铺路筑桥的善人呀!”李鸿章说得有点漫不经心,语音也极平和,明明是在和老朋友们说家常话。
“托总督大人的鸿福。”几个自以为在天津有过善举的商人们忙着站起来,向李鸿章拱手敬礼,然后又自谦地说道:“总督大人治理天津有方,才使我辈于经商中得以发展,生意上有了一些盈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训,我们总还是不敢忘记的。”
“可敬,可佩。”李鸿章颇为赞赏地说着。停了一会儿,他又向商人们询问:“据阁僚们对我说,天津富贾之中,有一位因行善举而感动上苍,一夜之间竟在他为民修筑的桥头,突然生出了五株古槐,真有这样的事吗?”
“这就是余隆泰大人亲历的奇事。”商人们一齐向李鸿章介绍着,随之,余隆泰也就从商人堆中走了出来。
“隆泰一介商贾,实在不敢自诩是行了什么善举。筑桥的事是有的,一夜之间,桥头岸上立起五株古槐的事也是有的。不过,感动上苍,隆泰自知无此功德。承蒙民众感激,一夜之间有人将五株古槐移来植于岸边的事,也许会是有的。恩泽在天么,也就只说是天赐了。”余隆泰自然不会相信苍天赐他五株古槐的神话,他心中早就估摸,这说不定正是自己身边的一个要讨好自己的人,悄悄地做下的一件奇事。据他推测,很可能是他家的仆佣班头,他最贴身的家佣,吴三代。
“余大人筑桥济世,感动上苍,赐福五株古槐;倘若余大人铺上一条铁路,那天下人就更要感激余大人的恩德了。”李鸿章说着说着,就把话题拉到修铁路的事上来了。
“总督大人过誉了。”余隆泰忙向李鸿章施了一个大礼,然后才又说着,“隆泰不过小有积蓄罢了,筑桥的几十万两银子,尚可倾其所有;用于修筑铁路,那实在是杯水车薪。不过呢,请总督大人宽恕隆泰放肆,依隆泰之见,这修路一事已是大势所趋,早修路早富国,迟修路迟富国,这来日的国运,已是和修路休戚相关了。”
“高见,高见!”李鸿章听到天津商界之中居然有人对修路持如此积极的态度,自然十分高兴,一反他直隶总督大人的种持常态,他竟对自己治下的一个子民,表示钦佩了。
“那,余大人就说说这修路的利端吧。”李鸿章本来给皇上陈奏过修路的《妥议铁路事宜折》,在这个奏折中他力陈筑路的好处。只是皇帝面前的一场争辩,把李鸿章的奏折给打入冷宫去了。反对筑路的人说修筑铁路是“祸国殃民,莫大乎是”,更有人对皇帝说“睹电杆而伤心,闻铁路则掩耳”,修筑铁路已被视为是大逆不道了。如今,听见余隆泰把筑路和国运连在了一起,李鸿章倒想借天津商人的嘴,再替自己说几句话。
“修筑铁路一事,事关重大,隆泰也知,朝中有人力主反对……”
“隆泰兄,反对修铁路的,可是醇亲王呀!”不知是谁,从后面抻了一下余隆泰的衣角儿,提示他说话要当心。但余隆泰此时正在气盛,何况他又是无官一身轻,无所顾忌,他回手推开背后拉他衣襟的那个人,口若悬河,他就说起来了。
“修筑铁路,实为富国之本,中国幅员辽阔,铁路一通,其利于漕务、賑务、商务、矿务之处,已不可殚述,且于列强觊觎天朝的今日,也是抵御敌军的当务之急。隆泰虽孤陋寡闻。但对朝中反对修筑铁路之说略有所闻,其铁路足以资敌之论,实为多虑。强敌入侵,固可以铁路而长驱直入,而我王朝,又何以不可以铁路而调兵遣将?铁路告成,声势联络,血脉贯通,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而夕至,十八省兵力合而为一。此时洋人再多,也敌不过我百万之众,资敌乎?御敌乎?有目共识,真是何虑之有呢……”
“好,好,你说下去,说下去!”李鸿章越听越爱听,越听越高兴,他已是连连击掌,在给余隆泰鼓劲了。
余隆泰做上了三井洋行的中国掌柜
余隆泰一马当先,鼓动得天津商人做了李鸿章修筑铁路的经济后台。第二年,李鸿章就组成了天津铁路公司,从天津商界筹到筑路用款150万两,再加上向英国又借了一笔路款,这修路的工程就开始了。到了公元1892年,光绪十八年,天津建成了老龙口火车站,从此,天津就成了全国第一个铁路中心。
因力陈筑路,余隆泰结识了李鸿章,李鸿章在天津筹措路款,余隆泰又几乎到了砸锅卖铁的程度。由此,余隆泰更是攀上了官府,他也就更平步青云,福禄双全了。
因为天津通了海运,通了火车,各国金融、商界便从四面八方向天津云集,而在这当中最是来势凶猛的,当属日本财团。
中国的门户,是英国人用大炮打开的。天津设埠通商,始于公元1860年,咸丰十年,那一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城,火烧圆明园,迫使清廷签下了《北京条约》,应允“天津口克日通商,洋船随便往来”。直到天津立了法租界、英租界、德租界、意租界,日本势力还没有挤进来。到了公元1867年,同治六年,天津已有洋行17家,其中英商9家,俄商4家,德商2家,美商和意商各1家,唯独没有日商的洋行。
看着英、法、美、德、俄在天津办洋行,做生意发财,日本人急得双脚乱蹦。他们想挤进中国,挤进天津,向英、法、德各国势力求情,让他们从瓜分中国的宴席上分给日本一杯羹。那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只好打通中国官府,来一个半路上杀出
个程咬金,楞往里挤。
于是,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年,日本在“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国策下,发动了一场甲午海战,这场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结束。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奉旨,带着他的儿子李经方,在美国顾问科土达的陪同下,前往日本谈判求和。4月17日在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中国设厂,并允许日本货物一律免税。由此,天津,以至中国的大门,才被日本人一脚踢开。
洪水一般,日本势力一下子涌进了天津。1898年,就在英国、法国在天津设立租界地40年之后,日本人也在天津设立了租界地。而且日本人不来则罢,来了就要称雄天下,天津的租界一次就占地1667亩,成了天津最大的一个租界地。立了租界地,立了领事馆,来了日本侨民,随之就办起了各种各样的“会社”,办了洋行,又设了横滨正金银行、大东银行等等金融机构,未及二年时间,日本人已经在天津打下根据地了。
在日本开设的洋行中,有一家最大的洋行,那就是三井洋行。
三井洋行,全名是“日本国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明着是私人资本,内中有日本国的势力,是日本的一家大垄断商行。尤 其是对中国,三井洋行垄断一切对华贸易,一切日本国对中国出口的物资,以及一切日本国与中国来往贸易,统由三并洋行经办,而且垄断海运和保险,结算战争“赔款”,代理日本国对中国的官方贷款。所以,这三井洋行,已经就是设在天津,以至于是设在中国的日本国了。
三井洋行既然设在中国,那就要有一位中国掌柜,而且三井洋行设在天津,还要有一个华帐房,只是这位三井洋行中国掌柜,应该由谁出任呢?
当然,不能是中国官员,中国朝廷里的官员不能在日本人开的洋行做事,无论什么职务也不能担任;还不能是中国官员的亲属,李鸿章的弟弟、内弟、还有他的儿子,都不能出任日本洋行的中国掌柜。那样就有了暗中与洋人沟通的嫌疑了,再在皇上面前说话,无论是说日本好,还是说日本坏,都不理直气壮了。
那么,就找一个商人吧,也不行。既然人家日本三井洋行方面有日本国的背景,这位出任日本国三井洋行中国掌柜的中国人,也得有点中国官方的背景。否则,人家有什么要和中国官府说的话,一个普通的商人,怕身份不够。而且,这个人还必须名声好,受人敬重,还得有学问,多少沾点儒门的边,虽说不是圣人吧,也得是位贤达。寻来寻去,这个职位在天津只有一个人能担任,那就是余隆泰。
当李鸿章一张帖子把余隆泰请到私人府邸,酒席之上,三巡老酒下肚,在李鸦章把推荐说出之后,余隆泰毫无准备,一时之间,竞把举到唇边的酒杯停在了半空,好长好长时间,他没有说出话来。
“身负重任,这个职位,已经是非公莫属了。”李鸿章劝导着余隆泰说。
“承蒙合肥大人错爱,隆泰自然是感恩不尽的。”把这样一个发财的肥缺送到自己手里,余隆泰当然知道这是李鸿章对自己帮他修铁路一事的报答。做上三井洋行的中国掌柜,那就是白银往家里流的差事呀。多少人上万两的银子送上去,未必能运动下来一个小小的盐务,如今李鸿章一句话便把余隆泰推到与日本人共分中国财产的位置,这该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呀!只是,余隆泰也明白,出任三井洋行的中国掌柜,从此自己就是半个官商了,自己因修五槐桥换来的名望,弄不好就要葬送在这个洋行买办的位子上,和洋人沆瀣一气,那不明明是在做卖国生意吗?
李鸿章历来是贵人话少,他“举荐”余隆泰去三井洋行出任中国掌柜,也无须向余隆泰交代这个差事是何等的重要,一切心照不宣,该如何办,由你余隆泰自己想去就是了。
本来,余隆泰还要推辞,但是李鸿章端起了茶盅。中国官场的规矩,这叫“端茶送客”,原来客人来时献上的那杯茶:是准备用来送客时用的。看见李鸿章端起茶盅,又听见李府
的老仆在门外高声喝唱:“送客”,余隆泰不敢怠慢,忙起身施礼,向李鸿章告辞出来了。
回家的路上,坐在自家的轿子马车上,余隆泰既为自己得了这份发财的肥差而庆幸,也为自己做上了买办而懊恼。去三井洋行做中国掌柜,明明就是李鸿章给了余隆泰一个发财的机会。在此之前,余隆泰经商起家,靠的是自己的本事,自己的运气,但出任三井洋行中国掌柜,那就不能只靠个人的能耐才干了。李鸿章的“举荐”,就是一道总督的大令,虽没写成文书,但却代表官方。日本势力初来天津,他们知道谁能胜任这个要职呀?而且,甲午海战后,李鸿章率子去日本议和,割地之惨、赔款之巨,已是举国为之谅骇,国人无不痛骂李鸿章卖国。当时竞有人传说,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已被日皇选为驸马,李鸿章已和日本皇室联姻了。四川一个不怕死的读书人上书李鸿章;开宗明义第一句便是:“人谓公一日不死,则天下一日不平。”可见,李鸿章的名声,早就臭到了家。
只是,日本人听李鸿章的。日本三井洋行初到天津设行,他们在选用中国掌柜一事上,是唯李鸿章的“举荐”是从的。余隆泰大半生清白,如今被李鸿章扔上了这条贼船,他的苦衷自然也是有口难言了。
余隆泰于到三井洋行就职之前,先去了两户人家,一户是他的亲家公,天津府的黄道台。黄道台自然是官职在身,李鸿章是他的上司,就只对余隆泰说些要尽心尽贵,不可辜负总督
大人的思泽呀之类的话;余隆泰去的第二户人家,是天津的圣人,严复。严复是位大学问家,是余隆泰家几个孩子的老师,也是余降泰的莫逆。严复一贯力主维新,他倒不认为做上了三井洋行中国掌柜的职位,便一定是参与了卖国行径。丧权辱国的罪魁是腐败无能的清朝朝廷,明眼人是不会把卖国的罪名推到与洋人经商,为洋人做事的类如余隆泰这类人物的身上的。
“好自为之。”严复只对余隆泰说了四个字,便和他说起几个孩子读书的事了。
三井洋行,好大的财势,余隆泰到任未及三年,一跃就成了天津的首富,而且人家三井洋行和中国人做生意,处处都恪守儒商之道,进一船货,出一船货,规规矩矩给华帐房提二成的利。那就是说,这一年之中,三井银行无论有多少盈利,落在余隆泰名下的就有二成。这二成的利润,除了华帐房的开销之外,余隆泰个人得多少,那就不必细说了。
自从余隆泰攀上了官府,成了天津的显赫,随之他就成了天津府衙门的常客。他找天津府道台大人不论朝政,不谈经济,只一件事,下棋。
余隆泰爱下棋,在天津卫,余隆泰没输过棋,而且余隆泰最爱和名人、贵人对奕。不好好和余隆泰下棋,你就休想在天津立足。和余隆泰下棋,不让他胜,他就不肯走,有一次余隆泰楞拿一炮一卒赢了对手的双车双马,“余大人手下留情,我输了,我输了。口服心服。”何以双车双马会在一炮一卒面前服输?因为余大入胜棋之后一般情况要摆宴庆贺,燕窝鱼翅、山珍海味,对于输家,那是足可以安抚一番的了。
“他们敬畏我的财势。”余隆泰有自知之明,并深知仅凭一炮一卒而能胜双车双马者,于棋谱上实属绝无仅有。于是,他要找一位不敬畏自己财势,又不肯装败认输的人一决雌雄。什么人不敬畏余隆泰的财势,只有道台大人了。当然,这只是在天津卫,北京城里的皇帝老子也不敬畏余隆泰的财势,说不定还不把余隆泰看在眼里。找皇帝老子去下棋?听说光绪皇帝被囚在瀛台了。慈禧老佛爷也爱下棋,余隆泰当然不去,哪里有一个大老爷们儿跟一个大老娘儿们下棋的?笑话。
为了躲避余隆泰常到天津府衙门找道台大人下棋,前一任道台大人向朝廷呈送了请调的奏折。他没敢告诉皇上,天津卫有个余隆泰常于夜半三更叫开天津府大门来找自己下棋,他只推说天津卫地处九河下梢,民性刁钻,自己治理无方,要求调往他任。幸好这位道台大人会做事,他一份厚礼买通了李莲英的机关,由此才一道懿旨下来宣他进京,改任他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