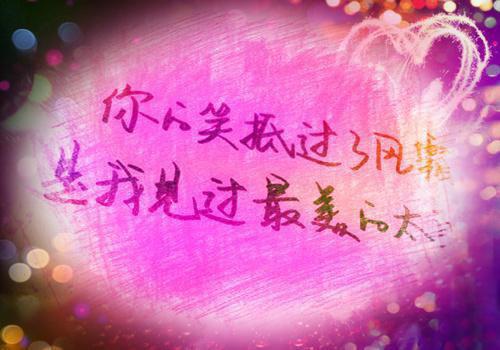五代那些事儿(套装3册)全文免费阅读_五代那些事儿(套装3册)最新章节
五代那些事儿.壹:朱温罢唐卷
朱阿三是谁
公元907年,中国历史的年轮进入五代时期。
翻开五代史,到处可见杀戮,满页皆是辛酸,套用一句小品中的火爆台词:为什么呢?答案:恶人当道。

有人会说,五代时期不是还有那么几个不怎么坏的人吗?比如后唐明宗李嗣源,虽然是一个胡人,却也有一颗仁爱之心;后周世宗柴荣,也称得上是一代英主。
这几个人是不错,在那个恶人当道的年代里,他们仍然能保持自己独立的节操;当整个中原已经变成炼狱的时候,他们也在尽自己的努力,想挽回一点儿人性的真、善、美,可惜的是,他们失败了。
李嗣源向上天祈祷:请上天派一个圣人下凡,拯救尘世间的黎民百姓。这就是说,他有一颗仁爱之心,却改变不了五代成为“恶人时代”的现实。
欧阳修老夫子写《新五代史》时,愤然摔笔,击案而起,大骂:“天下恶梁久矣!”
别说偷梁换柱,五代,就是一个恶人的时代。
五代的第一个恶人名叫朱温,小名朱阿三。
别看朱温篡夺了唐朝政权,坐上了龙椅,有模有样地做起了后梁小朝廷的皇帝,其实,他是一个素质低下、不讲仁义、不顾廉耻、纵淫无度的大恶人。
朱温出生在宋州(今河南商丘南)砀山午沟里(今安徽省砀山县),时间是唐朝大中六年(852)十月二十一日晚。据说,他出生的那天晚上,天显异象,“所居庐舍之上,赤气上腾”,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一片红光。邻居都以为朱家失火了,纷纷提着水桶,端着脸盆,赶到朱家救火。谁知跑到朱家门口一看,一切平静如常,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正在大家惊诧之时,朱家屋内传出了婴儿“哇、哇、哇”的啼哭声。
朱家生了个儿子。
汉高祖刘邦和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也都是天显异象。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通,是时雷电晦暝,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后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
汉高祖刘邦的老妈同蛟龙交合,进而怀孕生下刘邦——天生龙种,自然要当皇帝。只是这编故事的人,为了渲染刘邦的传奇身世,却没有顾及他老爸的面子——刘邦的老爸戴了一辈子的绿帽子。
赵匡胤出生时的“赤光绕室”和朱温出生时的“赤气上腾”,几乎如出一辙。
这些在书籍中偶有所见的异象,现实中谁也没有看到过。其实,这都是后世文人加油添醋杜撰出来的故事,借以渲染历史上这些皇帝,从他们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命中注定要当皇帝,要主宰天下。这是中国人“一切皆由天定”的传统宿命论在作怪。
朱温出生时的异象,载于《旧五代史》,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时,就没有保留这段文字。大概他觉得,这件事太悬乎,可信程度不高,所以就删掉了吧!
习惯上,乡下人给娃儿起名字,多叫阿狗、阿猫、阿牛什么的,他们都很朴素,认为给娃儿起一个贱名,可以无病无灾,好养。是否真的灵验,谁也说不准,千百年来,乡下人都是这样做的,习惯了。
由于这个习惯,乡下同名的人特别多,有时叫一声阿狗或阿牛,竟然会有几个人同时站出来答应。
朱温小名叫阿三,而没有叫阿猫、阿牛、阿狗,避免了后来做皇帝别人称他为猫皇帝、狗皇帝、牛皇帝的尴尬局面。
朱温的小名之所以叫阿三,而不是其他的,这要得益于他那个有知识的父亲。
朱温的父亲名叫朱诚,在砀山午沟也算是个名人。在乡下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讨生活的时候,他却在屋里教几个娃儿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说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朱诚是个教书匠。
朱温出生之前,他的母亲王氏还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朱全昱,一个叫朱存,也就是朱阿三的大哥和二哥。他排行老三,朱诚便给这个小儿子起个小名叫阿三。读书人的想法到底比文盲要丰富得多,他指望这个阿三能给家庭带来一些温暖,大名取一个“温”字,朱阿三又叫朱温。
朱温出生时虽然天显异象,但从他的身上并没有看到什么与其他孩子不同的地方,学步之前,也是满地乱爬,遇到一坨狗屎,照样要抓在手里好奇地玩半天。三五岁以后,仍然没有奇慧异秉体现出来,倒是舞棍弄棒的少儿天性展露无遗。他的二哥朱存也是一个闲不住的角色,兄弟俩拿着棍棒,同进同出,在乡里惹了不少事,害得朱老夫子经常给人赔小心。虽然经常遭到父母训斥,兄弟俩仍然屡教不改。倒是大哥朱全昱生性忠厚老实,待人彬彬有礼,颇显乃父风范。
朱诚的烦心事
朱诚有老婆、儿子,还有固定的职业,按说已经是很幸福的了,其实则不然,朱诚也有不少烦心事。他常对人说:“我这辈子熟读五经,靠教书糊口,生下三个儿子,唯大儿子全昱像我,二儿子朱存和小儿子阿三太淘气了,不知长大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啊!”
老夫子在为儿子的前途担忧呢!
朱老夫子是读书人,但他并没有强迫儿子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条路,或许是他觉得文化人这碗饭不好吃,因为他自己就过得非常寒碜,他不想儿子们步他的后尘。或许是他管理乏力,管不了儿子,否则,他的几个儿子就不会像野马一样,信马由缰,到处惹是生非。
儿子在外惹事,朱老夫子放下架子向人赔小心,乡邻们看在他的面子上,每次都能化干戈为玉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但是,有些事情,不是赔小心就能解决的。比如,每天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就超出了赔小心解决的范围。
老夫子虽然有稳定的工作、固定的收入来源,在山沟里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但他的日子过得并不怎么好。原因是,在那个穷山沟里,人们将一日三餐填饱肚子作为奋斗目标,而这些山里人连肚子都混不饱,哪有闲心、闲钱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呢?于是乎,老夫子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学堂的生源不足。
学生是朱老夫子一家的衣食父母,学生少,学费收入就少。儿子小的时候,饭量小,家里的花销相对也较少,靠那点儿微薄的学费勉强还能凑合。慢慢地,儿子们长大了,个个长得像小牛犊似的,饭量越来越大,朱老夫子的小日子过得就越来越困难了——吃了上顿没下顿,愁坏了老夫子。
粮食这玩意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要想得到粮食,要么,你就老老实实地春天去播种,秋天去收割,要么,你就拼命地去赚钱,用赚得的钱去买,除此之外,别无他途——除非你去抢。
朱老夫子是个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种田是外行,他的专业是教书,叫他去抢,他没那个胆儿。即使斗胆去抢,成功的机会也几乎等于零。可教书那点儿微薄收入,实在是填不饱儿子们的肚子。看着儿子们饿肚子,自己无能为力,朱老夫子非常郁闷,无可奈何。久而久之,竟抑郁成疾,一病不起,最后竟撒手人寰,到西天极乐世界去了。
朱家本来就是家徒四壁,连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没有解决,朱老夫子去世后,丧葬费就成了问题。可怜朱诚的妻子王氏,带着三个儿子,看着不能下葬的丈夫,哭成了泪人。幸亏乡邻们相助,东家凑几碗米,西家凑几个铜钱,好歹算是让朱老夫子入土为安了。
朱老夫子去了,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生活来源枯竭了,乡邻们救得了急,却救不了穷。无奈之下,王氏人托人、保托保,弄了份打工的指标,带着三个张口要饭吃的儿子,投奔到萧县的地主刘崇的家里当佣人。三个儿子也找到一份工作——做佣工,条件是包吃包住。一家四口,吃饭的问题好歹算是解决了。
无赖朱阿三
朱温一家四口来到萧县刘崇家,母亲洗衣、喂猪、做卫生,朱阿三和他两个哥哥放牛、种庄稼。
一家四口,从一个书香之家沦落为打工族。由于刘家只管吃、管住,连零用钱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所以,照这样发展下去,朱阿三发家致富的机会几乎等于零。
王氏对在刘家打工的这份工作相当满意,因为这份工作来之不易,也就格外珍惜。
朱阿三没有母亲那样容易满足,他的工作就是上山放牛,跟两个哥哥下地干农活儿,播种、施肥、除草,什么都干,每天从睡觉的破屋到田地,两点一线,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尽管此刻他还没有发家致富的念头,但至少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很乏味。
朱阿三不喜欢种田这份工作,他的特长是舞刀弄棒。放弃自己的技术专长,去干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此,朱阿三种田的积极性不高,干活儿没精打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要有机会,便偷偷地溜出去玩。
朱家兄弟三人,大哥朱全昱虽然任劳任怨,但体力不够,干不了多少事。二哥朱存虽然长得膀大腰圆,力气很大,干起活儿来却又是粗心大意——叫他去插秧,田里刚上水,秧苗就从水中漂起来了;叫他去锄草,连禾苗一同锄掉。朱温虽然很有力气,但为人狡猾懒惰,工作也不安心,而且,在刘家大院外面,他还经常干一些争强斗勇、偷鸡摸狗的事情。
争强斗勇,是一个性格问题,历史上扬名立万的人物,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倒也无可厚非,而偷鸡摸狗则就是道德品质出了问题。
中国有句俗话:从小偷鸡蛋,长大劫洋船。说的是一个人小时候小偷小摸,长大了就可能成为江洋大盗。
刘崇是一个土财主,不是慈善家。他收留朱温一家子,是要他们干活儿,当朱家三兄弟的工作态度、工作业绩达不到他的要求时,他就很烦;如果只吃不干,还在外面惹是生非,那就很恼火。他请的是打工者,不是门客,更不是大爷,因此,在刘家大院里,经常发生刘崇训斥朱温兄弟的事情。
每当老板发怒之时,老大朱全昱总是堆着笑脸,一个劲儿地赔小心;老二朱存自知理亏,也是甘而受之;朱温却总是狡辩,说我们哥儿仨也是人呀!总不能将咱哥儿仨当牛使唤吧!
一次,刘崇实在气不过,当众斥责道:“朱阿三啊!你成天吹牛皮,说自己无所不能,其实,你只不过是一个什么也不会干的窝囊废!你在我家打工,哪块田是你耕种的?哪个菜园是你浇的水?”
“雁雀焉知鸿鹄之志,宠物猫永远不知奔猫追逐的乐趣。”朱温不屑地说,“你看我是一辈子靠打工混饭吃的人吗?”
“什么?你吃我的、穿我的、住我的,还敢顶嘴?”刘崇怒不可遏,顺手抓起一根棍子扑向朱阿三。
朱阿三见刘崇扑过来了,忘记了老板与打工者的身份,一把夺过棍子,咔嚓一声,将棍子一折两段。
刘崇更加恼火,到处去找大棍子,恰巧被他的母亲看见了。老太太问道:“什么事呀?发这么大的脾气?”
“一定要打死朱阿三!一定要打死朱阿三!”刘崇嘴里一个劲儿地嚷。
“打不得!打不得!”老太太说,“傻儿子哟!你不要小看了这个朱阿三,他可不是平常人,前途不可限量啊!”
为何老太太如此看重朱温呢?这是有原因的。
据说,朱温刚到刘家的时候,曾出现过一件怪事。
一天晚上,朱温睡觉的屋子里突然传出一阵异常的响声,老太太被惊醒了,以为是强盗进门了,悄悄地爬起床察看。结果,看见朱阿三的床上盘着一条赤蛇,鳞甲森森,光芒闪闪。老太太吓得毛骨悚然,禁不住大叫一声。朱阿三被惊醒了,床上的赤蛇也不见了。
从此以后,老太太便说朱阿三是个贵人,对他格外照顾。她常对家里人说:“朱阿三不是个凡人,你们不要欺负他。”
刘崇的家人半信半疑,有时候也笑话老太太是老糊涂了。但笑归笑,老太太的话还是要听的。
刘崇是个很孝顺的人,母亲不允许他责罚朱阿三,也就只好作罢。因此,朱阿三虽然总是变着法子偷懒,却也能在刘家生存下去。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被中国人视为真理。
朱阿三虽然在刘家老太太的保护下,能在刘家生存下去,但他终究是一个无赖,无赖就是无赖,本性改变不了。
一次,朱阿三在外面赌博输了钱,欠了别人的赌账。晚上,他摸到刘家柴房里,偷走了刘家一口旧铁锅,准备拿去卖钱还赌债。其实,一口破铁锅,值不了几个钱,想必朱阿三是输急了,见柴房里只有这口旧铁锅还能换点儿钱,也不论多少,偷走就是了。
朱阿三的偷盗行为,恰好被管家发现了,他向刘崇告发了朱阿三。
刘崇带着五六个家丁连夜将朱温抓回来,绳捆索绑,关在柴房里,痛打了一顿。他大骂道:“朱三哟!我刘家待你一家不薄。供你吃,供你住,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为何不能安分一点儿呢?平日在外惹是生非,欺凌乡邻,现在又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
“怎么是偷呢?我是借,在外面赌钱输了,借你家一口旧铁锅还债,等我发财了,十倍还给你,行吗?”朱温的回答,让人捧腹。
孔乙己曾经说过,窃书不为偷,朱阿三将偷说成借,两人的狡辩,有异曲同工之妙。
朱阿三在历史上,是响当当的人物。英雄豪杰,固然不拘泥于小节,但偷鸡摸狗之事,终非英雄豪杰所为,因而,这件事成了朱温的政治污点,为后人所不齿。
朱阿三之所以后来被人说成是无赖、恶人,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刘崇听了朱阿三的回答,简直哭笑不得,本想将他痛打一顿,逐出刘家,偏偏老太太知道了这件事,赶来又救了朱阿三。
老太太有些恨铁不成钢地说,“朱阿三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不能再这样顽劣了,你不想种地,又能够做什么呢?”
“老太太!”朱阿三委屈地说,“隔行如隔山啊!”
“什么是隔行如隔山呀?”老太太不解地问。
“种地我是外行,也没兴趣,你们却要我成天同犁呀、锄头打交道,这就如同在我面前横着一座山。”朱阿三叫苦地说,“老人家,这座山我翻不过去啊!”
“你的专长是什么呢?”老太太似乎有些好奇。
“骑马射箭。”朱温说,“老人家,不如你给我一副弓箭,我每天去打一些野味回来,给你老人家改善生活,行吗?”
老太太乐了,笑着说:“我说孩子呀!你毛手毛脚的,给你一副弓箭,射着人怎么办?”
“老人家,你就答应我吧!”朱阿三知道老太太袒护他,故意哀求起来。
老太太是将朱温作为特殊人才对待的,经他一求,居然就答应了,只是吩咐他要小心,不要误伤了人。
那时候的大自然,完全遵循着一种原始的生存规则,各种动物优胜劣汰,公平竞争,人类对大自然虽然有占有欲,但火铳的普及程度并不是很高,要想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动物变成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只能用弓箭。那时也没有禁猎令,只要你有打猎的爱好,随时都可以行动——只要你对弓箭这门技术不是很外行,带着家伙出去走一趟,就不会空手而归。
朱阿三本来就是舞刀弄棒的高手,打猎也是他的拿手好戏,每次出去,都是满载而归。朱存看了心里痒痒的,也向刘崇要了一副弓箭,跟着朱温一起出去打猎,两人的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外面的世界很诱人
朱温摆脱了种地的羁绊,成了一名自由人,每天带着弓箭,到周围的深山老林里观风景,回家的时候,再射杀几只飞禽走兽,让刘家人改善生活,日子过得挺逍遥。时间长了,他渐渐地觉得又有些乏味了,想寻找一点儿刺激。
这一天,朱温来到宋州城外,正追逐一只野兔,忽然看见数百名士兵,护着两辆香车从大路走过,向前面的山沟里走去。出于好奇,他放弃了追逐的野兔,身不由己地跟了上去。
朱存见弟弟跟着香车走了,也跟上去凑热闹。
他们走到对面的山脚下,看到山上绿树成荫,半山腰的树林里,露出亭台楼阁,传出阵阵钟声,显然,这是一座禅院。
两乘香车走到山脚下,停住了,几名侍女从轿内扶下两个女人,前面的那位,是一个半老妇人,举止大方,却有官宦人家的气派;后面是一位大家闺秀,年龄十七八岁,容貌秀美,浑身透出青春的活力。
朱阿三猜测,这两个女人一定是母女俩,出自官宦人家,到这里来烧香拜佛。等她们上山进殿之后,也大着胆子跟了进去。
母女俩进殿拜过佛,由知客僧引着走向客堂。朱温快步走到母女俩前面,仔细端详那位年轻女子,见她长得果然漂亮,是他平生见到的第一美人。他不禁被女子的美貌所吸引,只是苦于在场的人多,自己身份低贱,不敢唐突。如果是在平时,换另外一种场合,他一定会找个借口,主动上前去同那位年轻女子打招呼。
今天他不敢,眼巴巴地看着母女俩在客屋里稍事休息后,在仆人的侍候下,走出寺庙,上车而去。
知客僧送走母女俩,转身正准备入内,朱温上前打了个揖手,问道:“请问师父,刚才那一双母女,姓甚名谁,家住何方?”
知客僧看了一眼朱温,淡淡地答道:“她们是宋州刺史张蕤的家眷,年长的是刺史夫人,年轻的姑娘是刺史的千金小姐。”
“是张蕤吗?”朱温吃惊地说,“他原本是砀山的富户,和我是同乡,如今做了宋州刺史?”
“听说要卸任了。”知客僧说罢,径直入内去了。
回家的路上,朱阿三问哥哥朱存,可曾记得父亲在世的时候说过汉光武帝的故事。朱存一脸茫然,不知道朱温到底要说什么。
朱温见哥哥回答不出来,自问自答地说,汉光武帝还没有做皇帝的时候,曾说过“为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这句话。
朱存反问道:“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朱温赞叹地说:“光武帝做了皇帝后,果然娶阴丽华做了老婆。”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朱存不解地问。
“你看张蕤的女儿,依我看,当日的阴丽华,也不过如此吧?”朱阿三色眯眯地反问道,“你说我能像光武帝那样吗?”
“刷了绿漆就当自己是块玉了?”朱存笑得几乎岔了气儿,讥笑道,“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说是什么意思?”
“时势造英雄嘛!”朱阿三生气地说,“刘秀是个什么官?有多少财产?后来不是做了皇帝吗?不照样娶阴丽华做了老婆吗?”
“你真是痴人说梦啊!”朱存笑道,“我们寄人篱下,有吃有穿就已经很不错了,还想什么娇妻美妾,你还是靠谱点儿吧!”
“二哥啊!”朱阿三说道,“你真是井底之蛙哟,你以为我们这样替人打工,就能发家致富、飞黄腾达吗?如果真是这样,天上真能掉下馅饼砸死人了。”
“你又能怎么样?”朱存也有些不服气。
“投军,做强盗。”朱阿三说道,“眼下唐朝气数已尽,天下乱成一锅粥了。前一阵子,听说王仙芝在濮州起事;后来,又听说黄巢在曹州起兵,整个东南一带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那关我们屁事?”
朱阿三道:“我们是勇士啊!”
“勇士又能怎么样?”朱存反问道。
“咱们投奔黄巢去,凭咱们的身手,在队伍里总能混出个模样来—— 抢一些财物,抢几个美女,总不是难事。到时,吃香的,喝辣的,多逍 遥,多快活!何必待在这穷山沟里,埋没了咱的青春,埋没了英雄呢!”朱阿三见朱存有些心动,继续说,“如果我们出去闹出一点儿名堂了,也 让那些瞧不起我们的人看看,谁是英雄谁是狗熊。”
朱阿三的狂想,引起了朱存的共鸣,仿佛一座金山就在前方,等着他去享受;仿佛外面有一个美人窖,等着他去销魂。两人一合计,决定到外面去闯荡江湖。
朱阿三、朱存哥俩返回刘家,先去禀明老母,说他们不想做一辈子打工仔,要出外去闯天下,讨生活。
当然,他们没敢说是出去当强盗。因为无论怎么说,当强盗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当母亲的如果知道儿子要去干这个杀人越货的勾当,说什么也不会答应的。
王氏尽管没有料到儿子想要出去当强盗,但突然听两个儿子说要离开自己,心里还是不舍,不放心地说:“儿呀!在家千日好,出外时时难。外面兵荒马乱的,找个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家人守在一起,虽然穷了点儿,为娘我心里踏实呀!”
“娘哟!”朱阿三说,“你儿子都人高马大的了,不能寄人篱下,给人打一辈子工吧!待在这里,不说发家致富,连个老婆也娶不起,你老人家心里难道真的踏实吗?”
朱温的话,搔到了王氏的痒处。三个儿子,都是人高马大的了,到现在还都是光棍,这是王氏的心病。
朱全昱听说两个弟弟要走出刘家大院,到外面讨生活,便问他们要到哪里去。
“现在还说不准呢!”朱温说,“大哥如果想去,咱兄弟仨就一起走,如果不想去,你就留下来照顾咱老娘吧!”
朱全昱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听说连方向都没有确定,当然就不想出去冒风险,便说他留下来照顾母亲。不过,他嘱咐朱温:如果在外面发达了,就带个信回来,到时,我再去投奔你们。
朱阿三、朱存当然是满口答应。
哥儿俩再去向刘崇辞行。
刘崇本来就厌恶他们,巴不得他们早点儿离开,只是刘崇的母亲迷信朱阿三将来会成大器,不仅吩咐他们许多话,还送给他们几吊铜钱,作为路上的盘缠。
兄弟俩收了老太太的一片心意和厚望,千恩万谢,辞别而去。